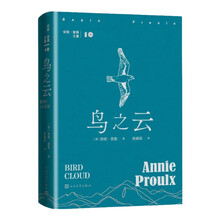在我21岁或22岁,也许是23岁时,我右手拿着一本书,登上了塞尔万多 尼街上那幢楼的楼梯。我在三楼停了下来。透过房门,可以听到钢琴声。我 倾听着。好像是德彪西的《前奏曲》,或许是舒曼的曲子,也许是福莱的曲 子,我记不得了。我等了一会儿。我刚按住门铃,乐声便戛然而止了。我按 下了门铃。巴特如同机器人般地停止了弹琴。这令我目瞪口呆。 在一番表示问候和欢迎的寒暄后,我们来到了厨房。炉子上正炖着什么 东西。我很喜欢我们共进的这些午餐,在他家里,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我 们的谈话比晚上在花神咖啡馆时要热烈一些。在中午,情况就不一样了。厨 房很窄小,必须不时起身开锅,找盐,取盘子,切面包,谈话就在日常生活 之突如其来的、可笑的偶然中展开、持续、中断、停顿、扰乱(以及吞下): 味道、声音、烧煮的时间、料理菜肴。我记得,经常会发生把什么东西烧焦 的情况。 巴特吃得很快,看起来酷似热内一样。热内是在监狱里养成这个习惯的 ,而巴特则可能是在结核病疗养院住院时习惯吃得很快。 他询问我这一周做了些什么,我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可汇报的:读书,间 或会有些极难归纳尤其是表达的想法。有时,我的身体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然后,轮到我向他提问。他同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好说。他很累。他谈起 了疲倦,有关睡眠的问题。不是睡得不好,而是醒得不是时候,总是在天亮 前突然醒来。我们还谈起了朋友们。那些最亲近的朋友。如果谈话很投机的 话,我们会玩一些幻想游戏:尤素福有时成丁劳伦斯·杜莱尔作品或《一千 零一夜》中的某个人物,有时又突然变身为韦尔迪兰夫人,即《恋人絮语》 中那个天真、倒错的提供消息者;有时又成了勃朗蒂姐妹或波伊斯某部小说 中的人物保尔,而更多的是成为贯穿《没有个性的人》全书的人物或克尔凯 郭尔哲学小说中的人物让一路易,尤其是因为他确实是个梅什金王子;至于 弗洛朗斯,不知为何,她使我想起了吉罗杜小说里的某个女主人公。巴特不 由得笑了,他更希望此刻她的名字叫苏珊。 如果恰逢某一个节日,用他的话说,幻想游戏使我们与人际关系网络的 次要圈子发生了交错,那么这种游戏便会维持一段时间。其他的面孔,其他 的人物肖像,关于普鲁斯特或其他人的玩笑(例如,有一位叫邦当的,因为 阿尔贝蒂娜的姑妈的缘故,曾经长久地成为我们午餐时的小小谈资)。 不过这一切很快便中止了。一阵沉默之后,我们转向了其他的话题。我 认为这种保留犹如疲倦的信号,似乎是对话的近乎戒律般的规则。对于极少 喋喋不休的我而言,我应该抑制住因年轻气盛而来的滔滔不绝,适应于一种 极为节俭的躯体、呼吸、语言方式,因为对方显得疲惫不堪,很快就衰竭了 。 他对“学院”颇多怨言,不过却从未因接受米歇尔·福柯的建议进入法 兰西学院而感到遗憾。他说,福柯“在机构里有非常强的政治关系(也许确 实如此)”:占据、介入、控制。万森纳(Vincennes)经验的规划失败(可能 是因为过于单义,过于天真的脱离社会),使他转向了另一种场合。巴特似 乎对于自己人选法兰西学院的政治意义无动于衷,尽管这个问题在他的开课 仪式上就已存在。不过,在我看来,正是在他把文学教育定义为“将对专家 政治的诉求压力与学生的革命愿望之间的关系扯断,直至对其厌倦”时,形 成了令人惊愕的时代错误。当时的我还是个年轻的学生,我很清楚这些词汇 已经不再有意义或者说明不了什么了。 其实,巴特试验过自己计划的有效性,这计划就是无听众的演讲,即和 某些缄默的亚洲学生一样,现场的听众个个噤若寒蝉,屏声息气,温顺无语 ;或者更为简单且充满了亲切气氛,因为在场的都是朋友们。在他看来,这 次实验是一个失败。 也许,他对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研究班”念念不忘;老师坐在门生们 中间,门生们围绕自己的景象与圆桌骑士的情景一样充满了睿智,甚至连那 张纤美的空椅子也浸透了学识。 作为法兰西学院梯形教室里的演讲者,其地位不允许他再次对学生们的 赞同和评论提出问题。他因此而抱怨不已。 其实,抱怨不过是对话的自然调节之一种而已。抱怨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情感关系要求朋友不得在听到抱怨时表示不满;这并不会使朋友关系因此 而不诚挚,但却破坏了关系中的心理结构,从而消解了责备(人们本来可能 对他的抱怨发出的责备)。 法兰西学院是一个唯有时间才能使其解脱的陷阱,他说。听众“令人厌 烦”。人数太多,他就像是走进了剧场。甚至连学院所在的街区在他眼里也 是“不讨人喜欢的”。我无法想象,他居然会希望自己退休。这令我这个年 轻人恐慌不已。 餐后点心就放在桌上。通常,是一个由他耐心削去果皮的水果。我们抽 着烟,啜着用意大利式咖啡壶煮就的咖啡。他抽的是一支中号哈瓦那雪茄, 而我吸的则是带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我们继续聊着天,因为只有在这时我 们才会重新谈论此前被忘却的事情。咖啡因和尼古丁唤醒了这些模糊的回忆 。一切突然变得从容不迫,仿佛这世界就是为了吸完一支“好雪茄”而存在 ,让那蓝色的氤氲缭绕着我们的身体。这些重新提起的话题是简短的,为数 不多,但通常都是一些“好消息”。他告诉我订到了某场音乐会的座位,或 者是我买到了歌剧院的票子;当时我即将完成他让我为《艾奥迪百科全书》 撰写、而他将联合署名的“口语/书面语”词条,他建议我和他一道去摩洛 哥度复活节假期(后来我们没有成行);一个美国研究小组正在开发一种以解 读《S/Z》的五个代码为基础的信息程序(即超文本的初级阶段,而巴特并 不知道,其实他自己就是超文本的首创者……)。 我们把盘子和碟子胡乱地堆放在洗涤槽里。有一个姑娘会在不知什么时 候过来打理①。他去午睡了。他看了我一眼,想知道我是否也打算去歇息一 会。当他缓缓走进里屋,他母亲曾经生活并在那里去世的那个房间时,我来 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会用看书或弹钢琴(加了弱音器)来打发他睡觉期间的这 一小段无聊时光。 这种午休,诚如我介绍的那样,源于他的肺结核病,始于他患病的那个 遥远时代。这种病,与其说是病,还不如说是一种状态。午休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延续,宛如无可救药者周而复始,宛如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去而复返。因 为,午休同样属于文学界的专利,属于纪德的专利。从杰出的《小妇人手记 》中,我读到了关于午休的趣味盎然的描述。P3-6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