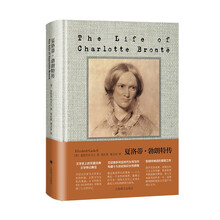辛弃疾词集里可以比较确切地推断为在江阴写的新词是这样一首:
满江红·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按字面理解,这首词像是描写一位少女伤春怀人之情的作品,但仔细品读,可以发现它似是通过艺术象征的手法,寄寓作者的政治感情。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此词:“可作无题,亦不定是绮语”。这是猜测它不一定是写男女之情,而是另有寄托。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于本篇编年说明中云:“其下之‘一番风雨,一番狼藉’,盖即指符离之惨败而言。”结合当时作者的心态和张浚北伐刚刚失败的时局来看,这些推断是很有道理的。
词的上片着力铺写暮春花残粉褪的狼藉景象,政治感情已暗含其中。首二句,交代自己由北人南,寄居江南,已过了两个春天的经历。“又”字下得极切,光阴蹉跎而壮志未酬的悲慨已寄寓于此中。以下风狂雨猛、百卉凋零的暮春之景,既用以暗喻当时政治、军事局势,暗指抗战“春光”已逝,同时也为下片专门抒发自己的怨情先做一番铺垫。“算年年”二句,更是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美好愿望一次次落空的心情。
词的下片,借助对深闺女子怀春之情的描写,来寄寓自己政治上的孤愤。“庭院静”者,政局万马齐喑,没有事业发展的动静可言。“空相忆”者,在此环境中,空盼好消息而不可得。“无说处”二句,进而倾诉自己政治上缺少知音的苦闷。“怕流莺乳燕”二句,意思更为含蓄曲折:闺中人怕多嘴的莺燕得知心事,正应合辛弃疾这个北方“归正人”险恶的政治处境,是他在上孝宗皇帝书中所自陈的“臣孤危一身久矣……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这样一种畏祸心态的形象化展现。南宋朝廷对这位北方壮士的忌刻之深和投降派小人的谗言之多,于此可见一斑。闺中女子所日夜盼望的“尺素”,自然是喻指有关抗金大业的好消息。而女子所哀伤的春去不归,显然关合作者心中所想的时机空失,理想未能实现。词的末二句,以景结情,以女子怕登高楼只见碧野不见情人,更深一层地表达了作者对国事的失望。由上面的分析可见,这首词的主题是抒写辛弃疾的爱国幽愤,但它与作者通常在抒发这类情感时习用的直抒胸臆和大发牢骚的做法有所不同,采取了曲喻的笔法,风格是含蓄柔婉的。
由上面这些词作所反映的情况可见,辛弃疾与南宋朝廷之间的关系,真是如常言所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为辛弃疾始料所不及的是,南宋朝廷是一个极端腐朽、极端软弱无能的卖国政权,因而他虽然满腔热情地南归于宋,倾其全力奋斗了大半辈子,却未能实现其北伐中原、统一祖国的远大政治理想。
以后的事实证明,辛弃疾想从南方打回山东、打回中原的梦落空了!
这是因为:辛弃疾虽然确实是一个堪当国之栋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不幸的是南归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大展鸿才的机会和环境。他南归的当年夏天,老玩家宋高宗赵构做了三十五六年的偏安皇帝之后,有些厌倦了,想退位了好有闲暇天天去西子湖玩儿去。于是在接见辛弃疾之后不久,就自称太上皇,将金銮宝殿让给了他的过继儿子赵奋,是为宋孝宗。这位孝宗皇帝即位之初倒有一番雄心壮志,立意要用武力北伐中原,胜利后还于旧都。第二年,赵奋听从了主战派大臣张浚的意见,起用他为枢密使,由他调遣军队北伐。张浚是一个言大而夸的书生,将略并非其所长。他用李显忠和邵宏渊为正负主帅,命二人统军渡淮北上。北伐军初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进展,之后正负主帅之间及二人所统领的两支军队之间产生了矛盾,将佐之间不能再上下相辖,士兵更因犒赏不均而失去了斗志。及金朝大军开来,宋军在符离(在今安徽宿县)竟然不战自溃,士兵和丁夫等13万人竟全都掉臂南逃,蹂践饥困,死亡无数,器甲资粮也全部丢弃,以致南宋政府若干年来所积储的军需物品一朝扫地无余。消息传回后方以后,主战派人物陆续被排斥出南宋政府,主和派、投降派的人物又在南宋朝廷里高高地昂起了头,他们的求和、投降理论一时又甚嚣尘上了。
在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人物因北伐战争失败而纷纷引咎辞职、离开朝廷之后,南宋朝廷里新的当权派决定派出谈判代表,向金人求和。他们与敌人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所谓“隆兴和议”。这个卖国条约签订之时,也正是辛弃疾在江阴任签判已经期满之日。从此,在南宋朝廷里,主和派、投降派重新当权,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宋朝廷畏敌如虎,对金人一直采取守势,秉国者无人再敢言战。辛弃疾大半辈子的光阴刚好与这四十多年的抗金低潮期相终始,在那样一种低迷、压抑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抗战主张和恢复言论自然不会被采纳,他在政治上、军事上自然不能有所作为了。不但如此,辛弃疾作为一个从北方沦陷区南下的“归正人”,还不断受到南宋官场中人的猜疑、歧视、排挤乃至诬陷迫害。当权者明知他才识超人,就是不肯重用他。在因平息内乱或安抚地方而不得不利用他的时候,又对他严加防范,频频调动他的职差,以免他在某一岗位待的时间长了树立起威信和培植起私人的势力。于是他只好发着“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倦客新丰”)的牢骚,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宦海的底层奋力泅渡。在南归后的头一个十年中,他就只能担任着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府通判、司农主簿等这样一些“佐贰之职”。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被南宋朝廷派做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添差通判(通判,官名,为州府长官的副手,与知府、知州共理政事)。建康是南宋在长江下游的重要战略据点,在这座城市里既设有皇帝行宫留守,也设有军马钱粮总领所。辛弃疾来此就任时,行宫留守是史正志,军马钱粮总领是后来当了宰相的叶衡,他们在当时都是官场很显赫的人物。除这两人之外,此时在建康任江南东路监司等职的,还有在士大夫中很有才名的赵彦端、韩元吉(此人以后定居上饶,还会在稼轩的生活中出现)、严焕、丘崇等人。在这些社会地位很高而且赫赫有名的大官员、大人物面前,辛弃疾这个小通判显得微不足道,重要事务没他的份,只剩下两件事他适合做,而且几乎天天做:一是他身体强壮酒量大,要被经常拉去参与大官员们的游从宴会;二是官员们都知道他会写诗填词,要他到文酒之会上去参与酬答唱和。这两件事中,第二件对于他日后成为词坛大家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