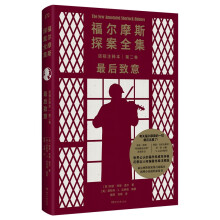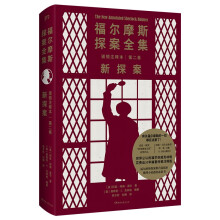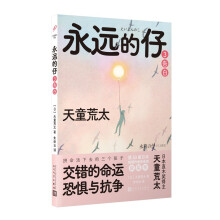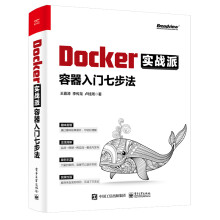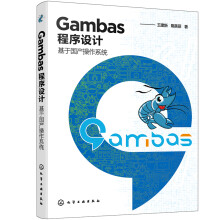在西伯利亚某处一辆呼啸的列车上,我上了有关战略的第一课。那时我八岁,正朝父亲肩头那边瞧着。父亲让我这么做的。他全神贯注地下着一盘棋。对手是个陷人沉思的老头,他双肩拱起,长而白的手指不断捋着唇上浓密的灰色胡须。慢慢地,老头一边嘀咕着一边从座位上朝前挪了挪,好像劲头上来了。“将!”他用意第绪语突然叫道,他的“卒”顶住了父亲的“王”。时间仿佛永远停滞住了一样,父亲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后来告诉我,他正在三种计策中权衡着。我记不起父亲是如何反攻的,或是谁最后赢得了胜利。然而,触动我的是两人的镇静和走每一步棋时的深思熟虑。他们好像没有听到车轮震动着薄弱的车身发出的那种铿锵节拍。雪霰“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并化成了水流缓缓地流淌下去,不过塞对两人并没有什么打扰。回首1940年年末的那一情景,一切几乎不太真实。两个男人下着棋,悠闲地思考着每一步棋着,仿佛占有了世上所有的时间,又无处可去,似乎除了这局棋赛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了。然而事实上,时间很快就逝去。我们是一车的难民,为了生存要逃脱纳粹的追捕。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啊,我们就仿佛是别人棋盘上的“卒子”。那场席卷欧洲的灾难将所有一切都颠覆了。什么种族、语言、观念和意识形态,全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并将我们这样的家庭送上流亡的生涯。我们还算幸运,家庭的主要成员——母亲、父亲和我仍然在一起,虽然有时饥寒,身体却依然健康。我不知道留在柏利斯托克的祖母们、我亲爱的玻波尔姑姑,还有我的朋友们,他们能不能侥幸逃出战争这头野兽的蹂躏呢?在我们沿着西伯利亚的脊梁——5800英里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进时,这段旅途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在这样一片完全未经涉足的莽原上,几千英里之内都看不到任何人踪兽迹,这辆除了汽笛不响什么都响的列车简直不值一提。在这一带寒冷的边远地区却蕴涵着一种美,一种粗犷的美。熊、老虎、黑貂、驯鹿、还有狼,自由自在地穿行在地球上蕴含量最丰富的几处自然资源宝藏之间。人们用“聚宝盆“来形容西伯利亚,这儿有全世界1/5的黄金和白银,1/3的铁矿和木材,还有数不清的天然气、石油和煤矿蕴藏。它又是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最大一片区域,40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整个美国的面积:满是沼泽的平原、茂密的森林、荒僻的高原还有峰峦嶙峋的山脉,这一切真叫人眼花缭乱,混淆了时空的界限。因为缺少道路,这辆跑在孤零零铁道上的列车,就是一种全能的运输工具,像是西伯利亚运输系统的载重骡马,又像是那时装满孩童和叮叮咣咣的家什、送着成群结队逃难的人们穿过欧洲乡间的牛车一样。虽然难民们惊慌失措,拉车的牛却始终不知道时间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紧迫。我们的机务长,好像同样不在意我们内心的煎熬。或许是为了省油,或许是因为天气,或许是路滑,列车速度不紧不慢,车轮的节奏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没有任何小路可走。确实是这样,因为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经常在指定的中转站(在乌姆斯、新西伯利亚或是伊尔库茨克)孤独地呆上个把小时,等待我们西行的同胞们经过,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我们的旅途直至西伯利亚的最东端——海参崴港。20世纪30年代,人们扛着铁锹、推着轮车,在斯大林建设苏联工业化的号召下建成了一座座钢铁厂。当战争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他们的工厂从易沦陷区迁往西伯利亚。也就是在这块地方,一些罪犯和政治犯被流放在矿区和劳动营中劳作;还是在这块地方,数百万人在战争前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死去,没有人知道。然而我不希望跑到故事前面去。回忆总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回忆开始,思绪奔腾而来。不过回忆也有神奇的力量。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点停下来,重新回想一遍,将那些陈旧的形象赋予崭新的意义。关于回忆还有一点,它是一道安全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