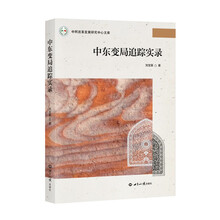第一章 我的青少年时代
童年在山西
1929年7月30日清晨,我出生于山西太原上马街。山西地处我国华北地区西部,整个山西省大部分是一个被黄土覆盖着的山地型高原,海拔在1000米以上。被称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就流经山西,因此我经常很骄傲地对别人说,我来自中华文明摇篮的山西。
我的父亲冀贡泉,字育堂,是山西省汾阳县(今汾阳市)建昌村人,1882年1月9日出身于一个农村教师家庭。我的母亲张陶然,又名冀顺心,生于1903年10月12日,也是山西省汾阳县人。她毕业于师范学校,是一位贤淑、文静的女性,擅长用手指作画。父亲在娶我母亲以前,曾有过两次丧妻之痛,所以我父亲和我母亲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很大。他们结婚时,母亲年方二八,而父亲已近不惑之年。我母亲为此在结婚前还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父亲长得很黑,又蓄有一脸长胡须。据说我父亲婚前去拜见未来岳父母时,我母亲偷偷地站在一张小凳子上,从门缝向客厅里看,想看一下自己未来的夫婿什么样子。没想到,不看犹可,一看是个满脸胡子的黑老头,吓了一大跳,从凳子上跌了下来。后来被她家人以三国时刘备染胡须和孙权的妹妹孙尚香成亲的故事说服,母亲终于嫁给了父亲。父亲的第一位妻子生了大哥朝鼎和二哥朝彝后去世,第二位妻子生了大姐慧青后又去世;我母亲生有三子一女,即三哥朝辅、四哥朝理、我和小妹妹青。
汾阳自然资源丰富,是汾酒的产地,也是山西省的棉花和粮食的生产基地之一,因为地处汾河之阳(西),故得此名。建昌村里明代建筑文峰塔是有名的文物古迹。父亲从小学习成绩优秀,1904年被山西大学堂录取,1905年被官府送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学习法律。他在日本留学7年,因为在班上名列前茅,所以小有名气。1912年,当局因辛亥革命停发留日官费,父亲拒绝接受日本政府的资助而中断学习回国。回国后父亲曾在教育部工作,趁公务之便,在日本又把明治大学法律系的课程学完,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后来他被山西军阀阎锡山聘为法律顾问,并历任山西司法和教育厅厅长。
父亲的性格极为仁慈。当官不久,他买了一支猎枪打猎。第一次打猎,他打死了一只鸟。他为这只可怜的小鸟伤心了很久。之后父亲就把猎枪扔了,而且一辈子再也没打过猎。
父亲慈悲为怀的性格大概是从祖父那里遗传来的。祖父是汾阳县建昌村的地主,荒年时他不但不催租逼债,反而开仓赈济穷人。在数十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三哥被遣送还乡,意外地受到家乡贫下中农的热情照顾,大概就因为我祖父的乐善好施所致。
父亲极富正义感,但同时胆子又比较小。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保皇党和革命党都要拉他加入,父亲说:“参加保皇党呢,怕丢脸;参加革命党呢,怕丢脑袋。”所以他两个党都不参与。父亲虽然胆小,但还是跟左派作家鲁迅交了朋友,二人后来成为莫逆之交。鲁迅日记中就有七处提及父亲。我小时候,父亲也曾一再对我们提起他同鲁迅交往的事。可惜我那时太小,对他同鲁迅的交往没有太深的了解,只是有这样一个印象:父亲同鲁迅是好朋友,二人经常来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父亲在山西任司法厅厅长,因为不满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父亲解散了司法厅,转到山西大学任法律系教授。1930年,父亲作为阎锡山的代表,到北平参加了汪精卫、冯玉祥等反蒋国民党人的会议。他们试图通过制定宪法来抗拒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的企图,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父亲认识到,没有坚强的政治基础,而只通过草拟一纸空文就想改变政治现实,那才是“最愚蠢不过的”。那时,通过我大哥朝鼎,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已有所了解。从那以后,父亲更加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来,阎锡山说服父亲重返省政府任教育厅厅长,父亲在他的岗位上多次保护了太原成成中学校长刘墉如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学生都上街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阎锡山命令父亲镇压学生,父亲于是用卡车强行把游行的学生拉到郊外,然后劝说他们以后别闹事,就把他们放了。但学生们并没有听他的劝告,被释放后继续游行请愿。阎锡山于是坚持要父亲调动武力向学生开枪,父亲拒绝执行阎锡山的命令,于是辞去官职,回到汾阳老家,过着隐居的生活。
父亲在太原工作期间,就在上马街买了一座砖头大院。我出生时,家中有七八个仆人。
在山西的那些日子,我可以说是天下最娇生惯养的孩子,因为我在兄弟里排行最末,而且身体最弱,所以最受父母宠爱。有一次上体育课,我在操场上差点儿晕倒。我当时利用长辈对我的溺爱,经常撒娇哭闹,每次哭闹都使我大获全胜。长辈完全满足我的要求,而惹我发脾气的人必然倒霉。专门照顾我的仆人名叫福海,他心地善良,性情柔和,对我百依百顺。我虽然体弱多病,但性情顽劣,充满好奇心。我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就是骑在福海的背上在太原城墙上跑来跑去,假装自己是抗拒从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的大将军。每值隆冬季节,我们就在院子里泼上水,等冻成冰后在上面滑来滑去。母亲很少给我们吃肉,我在院子里滑冰,每滑一圈母亲就给我吃一丝肉。
当时父母对我十分疼爱,我爱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但那时我只爱吃纯白面做的面条,什么蔬菜、水果都不吃,肉类也基本不吃,最多吃一点绵肉(即肥猪肉)或一两丝瘦猪肉。另外在六七岁前还每天喝一杯羊奶,那时我们家养了一只母羊。由于蔬菜、水果基本不吃,蛋白质食物吃得也很少,所以我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身体就更弱了。小时候因为缺钙,我的腿是弯的。幸好我9岁去美国后喝了大量的牛奶,才长得很高。
父亲把家迁回汾阳后,还是全县最有威望、最有地位的绅士,他的孩子们也顺理成章地进了全县最好的学校。父亲那时还有一把手枪,这是他权势的象征。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很快就推进到汾阳附近。那时汾阳虽然没有中国驻军,日军仍然对汾阳县城进行轰炸。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炸弹降落时的呼啸声和炸弹爆炸的巨响。幸好炸弹没有落到我家附近。随着战事的吃紧,人们开始大批逃离县城。我们学校怕学生都逃光了,于是宣布逃离者一律开除,永远不准回校。我四哥和我都很怕被开除,回家后就把这事告诉父母,父母都没有反应。但是第二天,我们全家就坐上了最后一辆卡车离开了汾阳。父亲深知自己曾留学日本,在日本小有名气,日本人来后一定会找他做事。他不愿当汉奸,所以赶快带着一家人逃往汉口。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等到35年以后,我才又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去山西帮助清理“反革命”,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出了汾阳以后,我们在黄土高原的小路上时而坐骡子拉的轿车,时而步行,有时还停下来躲日本飞机。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星期,才走到黄河在西南转弯的地方,也就是晋陕豫三省的交界处。我们坐一艘平底木船过黄河到潼关下船,过潼关时父亲出示通行证件后,交出了手枪。母亲告诉我们,父亲不再是在山西时那样有权势的人了,我们以后言行都要格外小心。
父亲本来已决定到邻近的陕北参加一年前刚完成长征的红军,但后来因得知我大哥朝鼎要在次年(1938)从美国回国,于是决定先到汉口等大哥。我们在1937年夏末乘火车到达汉口。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当地入学。一进校门,我马上就意识到情况和在老家时大不一样,到学校时,并没有老师笑脸相迎。我走进教室到书桌后坐下,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过班上的一个小霸王很快就决定要教训我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厉害。下课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把拳头在我鼻子前晃来晃去。幸而他穿的裤子太大了,他必须不断地用两只手提裤子以防裤子掉下来,这就给了我逃跑的机会。
我们到汉口后几个月,南京就陷落了。我们听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杀害,无数中国妇女被强奸后又被刺刀刺死。对日本军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感到十分震惊,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情绪空前高涨。那时,日本飞机又加紧了对汉口的轰炸,但因为我们住在法租界,日本当时同法国尚未开战,法租界就等于是法国的领土,因此相对来讲还算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人站在房屋外面的马路上看日本飞机轰炸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还击。忽然听到一阵欢呼,我们赶快抬头看,原来一架日本鬼子的飞机被打中了,冒着黑烟掉了下来,我们也都跟着欢呼起来。
祖父也跟着我们一起从汾阳到了汉口,没过几个月,他就因病去世,享年84岁。父亲后来告诉我说,祖父一生住在山西乡下,无法适应汉口法租界的生活方式,饮食也不习惯,所以一到汉口就感到身体不适。我想祖父去世虽然和水土不服有关,但主要还是老人眼看自己的家园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老百姓惨遭不幸,生灵涂炭,忧国忧民而死的。祖父去世后,许多权贵到我们家吊唁,这说明父亲当时在汉口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南京陷落后,汉口是临时首都。有几个官员告诉父亲说,蒋委员长想请他做司法部副部长,但父亲拒绝了。大概父亲那时已经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非常气愤。
此后不久,我大哥朝鼎就回国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大哥朝鼎和我的年龄相差很大,比我大26岁。他和我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在家时,常常同母亲在一起庆祝生日。我出生前几年大哥朝鼎就离家了。大哥朝鼎13岁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岁就和同学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16岁时他积极地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在1924年去美国深造以前,还同当时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有过一次长谈。李大钊鼓励他去美国学习,要他多学习对建设新中国有用的知识。后来大哥朝鼎在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于1927年在比利时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哥朝鼎在美国读书时,原来学习法律,入党后改学经济。他曾接受党的任务到莫斯科,为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周恩来当英文翻译,所以周恩来对大哥朝鼎很早就非常了解。大哥朝鼎那时已经同一位美国共产党党员结婚,并有了孩子。她是大哥朝鼎在去欧洲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在船上认识的,名叫海莉,出生成长在纽约。她的父母都是东欧移民。
大哥朝鼎这次回国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当时我对大哥朝鼎最深的印象是,他使我头一次尝到了冰激凌和黄油,这两样东西一直到现在都是我最爱吃的(当然我现在知道年纪大了不应该吃太多的脂肪)。
我还记得大哥朝鼎那时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跟父亲谈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和父亲主要是谈去延安根据地的事情。
不久,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大哥朝鼎把我带到长江边上。我看见一架水上飞机停在码头上,他和飞机驾驶员咕噜了一阵,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同驾驶员讲的是英文。几天以后,我们全家就把行李收拾好,坐上水上飞机飞往重庆。飞行的路上飞行员告诉我们有几架日本飞机尾随我们,我们赶紧在长江上降落。我们都跑到岸上,藏在一个坟地的灌木丛中,在坟墓旁平平地躺下,一直躺到日本飞机飞走了。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然后才起飞,终于安全地飞到了重庆。
一到重庆,父亲和大哥朝鼎就着手准备去延安,而且开始安排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见面。可惜大哥朝鼎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做手术,所以我们就误了去延安的车队,而且需要等很久才会再有一次去延安的机会。如果我们单独去延安,就会特别危险。当时,周恩来找父亲和大哥朝鼎,向他们提出,也许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全家都去美国。当时周恩来就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在美国工作,做加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许会对中国革命更有用。当时我们家有一些特殊的有利条件,就是大哥朝鼎对美国相当了解,他的英文非常好;父亲对日本相当了解,日文非常好,而且英文也不错。那时汉口也被日军攻占,重庆变成了战时首都。父亲认识国民党中央政府很多教育和法律部门的高级官员,所以他那时给我们一家都办护照还是比较容易的。他去美国的表面理由是去研究西方法律。
一切都安排好后,父母、大哥朝鼎、四哥朝理、我及小妹妹青就动身去美国。家人中还在北平读书的三哥朝辅、已结婚的大姐慧青以及在绥远念大学的二哥朝彝未能同行。
我们先从重庆乘飞机到昆明。这是我第二次坐飞机,但还是很兴奋。和上次从汉口飞到重庆不同的是,这一次飞行不是太稳定,因为飞机很小,又要经过很多山岭,所以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我玩得很高兴,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因为那时飞机上还没有安全带。可是我母亲、四哥朝理和小妹妹青都晕飞机,所以他们感觉很不好。然后我们坐汽车、火车和轮船从昆明、西贡到新加坡,又从新加坡坐英国轮船横渡印度洋和地中海到法国马赛,走了大约一个月。最后再由法国的一个海口城市瑟堡远渡大西洋到纽约。父亲、大哥朝鼎和我一路上都过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在船上吃了很多好吃的,喝了很多汽水,天天像过节。可是母亲、四哥朝理和小妹妹青都晕船,因此过得很不愉快。
在巴黎我们住了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全家在巴黎有两大发现:一个是法国饭,尤其是法国的美味羊角面包(邓小平也很爱吃)和法国的巧克力特别好吃;还有一个是巴黎的女士年轻时差不多个个都漂亮得不得了,但等她们到了35岁后就会发胖,当然也就不漂亮了。
我小时候好奇心很强,对新的奇特的东西一直有很强的求知欲,这种好奇心一直跟随了我一辈子。巴黎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奇异的世界。我那时才9岁,刚从中国偏远的内地来,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妙的西方世界。有一天,我们全家散步的时候,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眼花缭乱,我左看右看看不够,把其他的都忘了。看了一会儿后就发现,前后左右都是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陌生人,我的家人却找不到了。我发现我走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放声大哭,可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在国外全家最重要的人是我大哥朝鼎,所以我就拼命大声喊叫大哥。我大哥朝鼎当时已经是很紧张地在找他的小弟弟了,一听到我叫就赶紧跑过来,这样大家才放下心来。
1939年2月2日,我们的船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港,大嫂海莉带着孩子来接我们。我还记得大哥朝鼎非常高兴地挥手大叫他的大儿子的英文名字--埃米勒!埃米勒!这一天就是我在美国11年半生活的开始。这11年半中,我小学毕了业,又上了中学,还上了两年大学。
现在回想起去美国的这段往事,我有时还非常感慨,人的命运往往是由一些偶然事件改变和决定的。如果当时大哥朝鼎没有生病,我跟着父母和大哥朝鼎去了延安而不是美国,我如今很可能就是延安的“三八式”老革命、老干部了。
在美国上小学和中学
我们到美国后,父亲和大哥朝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同大哥朝鼎的两位朋友、中共地下党员徐永瑛和唐明照在唐人街创办了《美洲华侨日报》,由父亲担任总编辑,徐、唐二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从旁协助。创建这份报的主旨就是号召海外的华人社团联合起来,并且同美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抵抗日本的侵略。该报一直延续至今,报道来自中国的消息,现在叫《侨报》。
我父亲在美洲华侨日报社的收入很微薄,每月还不到100美元。来美国前一路逃难,颠沛流离,随身带的钱财也都花光了。大哥朝鼎在美国有工作,收入不错,但他也要养家,无法给我们太多帮助,所以我们只能在纽约曼哈顿东城下区的贫民窟租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每月房租35美元,剩下用来买食物的钱和其他方面的消费就很少了。两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需要熟悉亚洲、特别是熟悉中国和日本情况的专家,我父亲应聘到美国政府战争情报署太平洋司任助理编辑。这份工作的收入当然要比原来的高得多,因此我们得以有能力搬到一处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位置在第十街的第一和第二马路之间,但仍未离开东城下区贫民窟。
来美国前,我从没想到会住进这样的贫民窟里。我们的新家在一个非常破的公寓里,公寓有六层楼高,我们住在最顶层。顺着又黑、又脏、又潮湿的楼梯爬上去,走进房间,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家具都是又旧又破的,墙上的白灰也脱落了,蟑螂满地爬。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呀,美国真穷啊!”可是后来我很快就意识到,实际上穷的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这个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