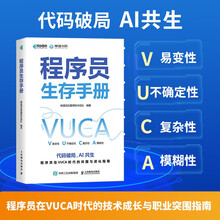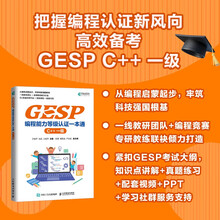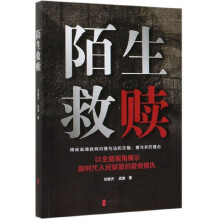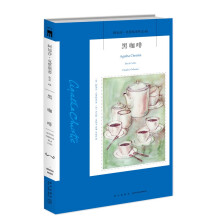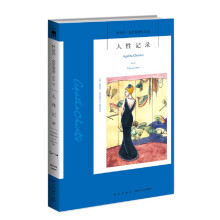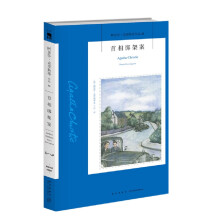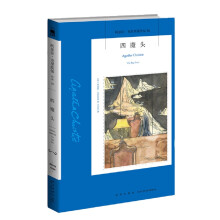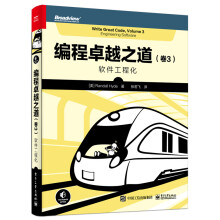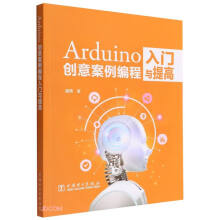因此,在随后的20年里,几乎所有戏院建筑的创新和管理都围绕着一个新原则,那就是实现一个共享的、没有阻隔的赏戏空间。从此,不同观众的社会等级不再明确地以社会地位或者阶级作为标准,而是以距离舞台的远近作为原则。这个原则仅仅是通过戏院的票价高低来实现的。这种全新的空间安排,天衣无缝地实现了在社会公共空间下人人平等且匿名的全新理念,而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观众赏戏时清晰的视野,因而可以说,该原则从此把艺术审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外,夏氏兄弟和他们的同僚还把剧院的改革当作整个现代改革的一个缩影:他们把原来低效的、不理性的、不公平的、且高度等级化的茶园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公共空间。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每个个体都能有相同的看戏权利和共享的观赏视角。为了保证每个顾客的平等权益,夏氏兄弟甚至试图减少“看座儿的”对戏院座位安排的干预,希望打破他们通过依靠联合精英、黑帮以及裙带关系而垄断好座位的局面。其他的改革措施也都主要集中在明确减少市场行为对观众物理空间的干扰,比如新的剧场修建了固定的售票亭,而小吃店则被挪到大堂位置,倒茶的服务人员在训练时被要求尽量保持低调,或者某些剧场则干脆取消了这项服务。通过把零售小贩还有领位员改为领固定薪金的剧场雇员,戏院的经理们可以确保这些人遵守剧场的新规定。戏院的新建筑布局巧妙地把观众的市场情结从他们的原有的赏戏行为中剔除掉了。如今,每个人在看戏的过程中都始终面对着舞台,那些诸如贩售、赌博或者和朋友高谈阔论的行为从此成了不礼貌的、分散注意力的、打扰戏剧正常进行的行为。从此以后,黑暗化了的观众席减少了赏戏者还有零售小贩在演出当中走来走去的可能性。
在1908年“新舞台”投入运营的一年时间里面,几乎所有上海的剧院都把他们的名称从“茶园”改成了“舞台”,尽管有时候戏园的空间结构并没有马上进行同步的变革。①在随后到来的改建大潮中,几乎所有的新场地都根据“新舞台”的改建模式进行施工,很多时候他们干脆采用了更现代/西方化的名称,即“剧场”来命名这些新落成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京剧茶园已经绝迹;而在北京,只有少数墨守成规的戏班还在老式的剧场里演出。戏院从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商品化模式,那就是作为商品的戏剧抑或是电影都必须在门口买票才能观看,并且在观众尊敬而被动的气氛中被消费。过去茶园那种如自助餐般自由的社会和商业活动,比如饮酒、聊天、仰头扭脖、扔手巾板等活动,如今则被纷纷诟病为“混乱”。②到1930年,以往的叫好也被许多批评家认为是粗俗不堪的,尽管很多时候叫好是对演出的一种礼貌的赞扬。这种喊叫,同谈话、吃东西、喝酒水、四处游荡以及在剧场里不脱帽的这些行为一起被认为是极其不文明的举止,更为那些有公共意识的公民所忌讳。西式剧院的建筑与其配套的观众行为举止规范一起,成为了彼时被争相模仿的对象。而那些先进的科技,比如照明,通风还有音响设备,则更是被争先恐后地采用。有的剧院甚至还在舞台上安装了脚部照明灯,这更强化了舞台和观众之间的分明界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