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维基解密的诞生
上路了。我曾有机会去很多机构内部观察,要么是去主动拜访,要么是晚上入侵系统,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户网站。不过2006 年我早就结束了这种黑客活动,我想要的是对付那些机构和政府组织,勇闯他们赖以生存的阴暗世界。我不是个很有创意的政治思想家,也从不这样宣传自己,但我懂技术,了解政府构架,准备好将政府扔到一盆酸液中溶化,只剩骨架。我有一种觉悟:我们可以沾沾自喜地生活,纠结于房贷、名望、财富、真爱,或者可以观察我们世界的骨架,测试它是否真的代表了真善美。
进入大多数机构后,你会看到它从权力和庇护中汲取养分,并借助营销手法自我保护。对我来讲,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事实,但后来的经验表明,大多数组织死活也不会承认这点。不管是肯尼亚政府还是瑞士宝盛,都在为自己谋利,他们建立起一整套狡猾的网络,成员一面从中获得好处,一面反过来支撑起网络,而普通人则被打入底层,处在劣势地位。自少年时代起,我就接触到庇护网络,对它背后的动因了如指掌。任何起来反对他们的个人或组织都会被法庭、情报特工、媒体弄得身败名裂。我已经做好准备。我已经磨练好技术本领,利用密码学的方法保护信息来源,保护那些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来源。我们作为活动家身经百战,拥有敢将皇帝拉下马的坚强意志。我们没有办公室,但有手提电脑和护照,在不同国家设立了服务器。我们深知,我们为全球各地举报人提供的平台安全程度史无前例。我们有顽强的勇气,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放马过来。2006 年10 月4 日,我注册了wikileaks.org 。我心里明白,自己普普通通的生活,如果真有过的话,从此会彻底改变。
我有一些帮手,也可以说是“先进典型”,比如纽约建筑师约翰?扬,他于1996 年创立了cryptome.org 。Cryptome 上不完全是泄露的文件,但扬始终致力于公布政府和企业不愿公布的信息。他们被微软攻击过,也和维基解密一样与贝宝有过争吵。Cryptome在信息大战中站在了正义一方,但他们没有一套针对数据提供者的保护机制,而我很清楚保护机制必须存在。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他不愿意做终极披露者,而这偏偏是我的目标,利用为维基解密完善的复杂否认系统来实现。工作进展迅速,我希望保证资料的保管和存盘万无一失。大部分筹备工作都是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的,一些老一辈密码朋克也出了一份力。我在数学系认识的老朋友丹尼尔?马修斯——他属于传统左派,可以算是一名乔姆斯基主义者——也在当时帮了我不少忙。丹帮我整理维基解密的创始文件,后来还为我们第一份泄露的文件发表分析评论。
我当时的工作是拉人入伙。我计划成立顾问委员会,为未来收集数据开拓资源。在这个阶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提高组织的可信度及为未来发展拉关系,没有实际办公地点,也没有起到顾问作用。我联络上了一些让人倍受鼓舞的重要人物,比如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就同意加入,并一直没有离我们而去。一位名为本?劳里的英国数学家也加盟维基解密,他父亲彼得?劳里60 年代出版过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城市街道之下》,讲述了英国地下核掩体和政府机构的情况,也许本在我们的工作中见到了父亲的身影吧。我也想联系一些中国活动家。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西方人,受西方法律的管辖,我不希望让人将维基解密视为一个反西方组织——这并不难,因为维基解密不是反对西方,而是支持信息传播——但是我清楚我们的靶子最终会放到美国身上。创立伊始,似乎显然应该先从非洲国家的腐败现象入手。自成立第一天起,我们的理念就是“反对混蛋”,听起来有些粗俗,但我们的真诚表露无遗。
启动前,注册域名等等所需资金都是我自己掏腰包的。其他人则是义务工作。自打一开始,我们就预料到今后会遭到法律上的攻击,因此我特别希望能在旧金山注册,因为旧金山的民权运动精神会在我们惹上麻烦时为我们摇旗呐喊。这一步完成后,接着就是给所有知道的人写电邮,等对方答复了。
第一份泄露的文件于2006年12月28日公布,数据源很神秘,因此我们也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当时索马里的局势在西方没有得到实际重视,而这短短两份文件就能让人看到当时的情况多么复杂。我们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尽可能提供分析、评论和其他泄露信息。即便文件是假的,它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证明秘密文件的披露能够加深我们对复杂政治局势的理解。对于维基解密这样一个刚起步的网站来说,这第一步棋走得很妙。
我们都对西方媒体的道貌岸然麻木了——更不要提东方世界很大一片地区严苛的审查制度——竟然忘记各国人民对自由出版和披露侵权现象如饥似渴。世界各地的人迅速给我们反馈,有些信息不可信,有些内容帮不上什么忙,但大家都开始关注我们的事业。当然了,因为我们是别人口中的“告密网站”,自从一开始就有某些人乐于告我们的密,一直都是这样。我的回答总是:“好吧。我们应该吃点自己开出的药,尝尝是什么味道。”我们是一群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十分理想化,努力改变着世界。别人的攻击我们承受得了,但我们最基本的道德立场稳稳的,想不出敌人还能怎样污蔑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对我的人身攻击,也没有想到憎恶我们的人会污蔑整个组织。有些神经错乱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面对着种种困难,我们依然勇敢前进。我想拉朋友入伙,但从个人经验来看,友谊只能带来约九个小时的免费劳动。要做的工作多到难以置信。运作理念是多年以来思考而成的,但编程、后勤等工作必须快速高效完成。我从肯尼亚走到坦桑尼亚再走到开罗,一路不停做网站,全部行囊一个帆布背包都装得下。坦白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也不是那么物质主义。衣服不多,手边有什么就吃什么。我留不住钱,钱一到手不是花掉就是给人。眼看着我这一代很多天才计算机宅人成为了百万富翁,我感到有些恼火,不是因为我也想发财,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向我伸出援手的。话虽如此,在成立维基解密的这几年里,四处飘荡的经历让我缓慢地意识到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物质需求。我有一袋子袜子和内裤,还有一个大一点的袋子装笔记本电脑和电线就够了。
我来到巴黎和伦敦拉帮手。很多志愿者短期内很踊跃,但后来不是想要钱就是要名望,我也理解他们的想法。在巴黎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两个月,当时恰逢尼古拉?萨科齐为竞选总统四处拉票。时间是2007 年春。我身心彻底崩溃,因为我知道维基解密有能力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工作太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忙碌,巴黎夜晚的街道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让人很容易忘记网站最终是真的有可能造福世界的。我当时的女友会时不时来我这里。她只负责给我送吃的,我则一直守在计算机前。她会讲俄语,有时我看不懂俄语会帮我一把,总体说来那段时间我是一个人熬过来的。我对工作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计算机半步。
有时候我觉得听到了屋外鸟儿的尖叫,自以为肯定是磁岛的热带鸟类。有时候我还在一瞬间幻想糖蚁在桌面、地面上列队爬过。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匆匆流逝,天气变得奇热,我还要保证维基解密的提交系统万无一失。当时我手上已经搜集了大量资料,但自建站之日起新信息就不断涌来,我向很多告密者保证日后会公布。因此,我一面按新数据的优先程度分类,一面又对系统修修补补,设计加密电邮系统,为比如肯尼亚人安全互动编写程序。感觉就好像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分部似的。和任何新生业务一样,维基解密必须要自我有机成长: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紧迫,因为这不是一家正常的公司,没有正常的筹资模式和业务模式,也不通过打广告和注入风险资本来运营。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一天到晚寻找志愿者,同时经常在网上与事先约好的人开会协商。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可没觉得有意思),有一两次只有我自己参加会议。整个流程看起来肯定就像是个精神分裂者在演独角戏:我坐在那里,敲着键盘,同时扮演主席和秘书的角色,一个议题接一个议题往下走,唱票表决。真是疯了。不过当时我认为自己必须要煞有介事地进行下去,坚持到底就是成功。出于这种自我鼓励的精神,有时候我还决定某项特定的工作——比如写一份重要的新闻发布稿——需要着装得体,体现出场合的严肃性。想象一下,我窝在巴黎一间狭小闷热的房间内,胡子拉碴,敲着键盘,身上却穿着得体的西服外套。有够离谱吧。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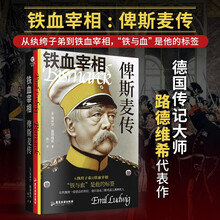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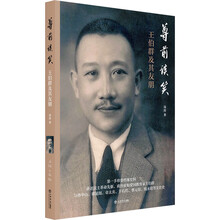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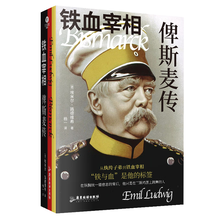

——《中国青年报》
40年来,我就在等另一个人来揭秘,这或许能给现状带来改变。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
维基解密所泄露的事情中唯一让人惊讶的就是其中没什么事情出人意料。难道我们了解到的不正是我们预见到的?真正惹麻烦的在于其呈现方式:我们再不能假装不知道那些人人都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这正是公共空间的悖论:尽管每人都知道某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在公开场合把它说出来便改变了一切。
——斯拉沃热·齐泽克
优美的叙述……他有些特别:好斗、易怒、才华横溢。无论他相信与否,书如其人。
——《泰晤士报》
一个非凡的故事,用令人愉悦的文笔塑造了一位古怪的英雄。
——《独立报》
尽管诞生于争议中,阿桑奇的这本自传却格外发人深省。
——《观察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