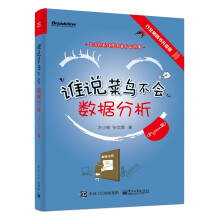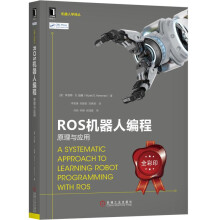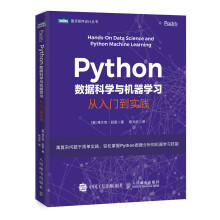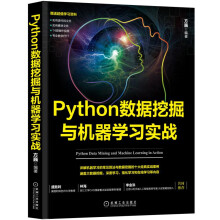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思考,是从内部和外部,或者说当时和后世两个角度展开的。内部审视主要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随着佛罗伦萨政治状况的变化,在观念上对共和国制度所作的反思。外部研究主要是后世持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从自己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意大利城邦的整体理解出发,对佛罗伦萨共和国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诠释。
首先整理一下“内部”线索,或者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共和国的认识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随着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rick II,1194~1250年)的去世(1250年)和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的衰败(1266年),意大利的城市取得了事实上的自治权。在这个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仍是为基督教精神认可的君主统治,它的权威基于中世纪人们对于两种秩序的认同:一是宇宙的等级秩序,二是家族的父权秩序。但是意大利的城市政权却违背了这种传统的秩序和君主权威,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一面复活了古典的共和主义,一面出于现实的需要发展了“主权”和“国家”的新观念。最早提出这些观念的人包括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约1220~1294年)、卢卡的托勒梅(Ptolemy of Lucca,约1236~1327年)和雷米焦·德·吉罗拉米(Remigio de Girolami,1235~1319年)。拉蒂尼在《宝藏篇》(Tresor)中认为共和制度相对于君主制来说是“最好的”,卢卡的托勒梅在他的《统治术》(Determinatio)续篇中不但表明了对共和的偏爱,而且认为意大利城市和希腊城邦的政治统治非常相近 。雷米焦则在《论公共的善》(On the Common Good)、《论和平的美德》(On the Merits of Peace)中提出“不是公民的人非人,因为人从本性上是一种具有公民性的动物”,“公民可以从公社的善中得到自己全部荣誉、威望和善”。
随着行会 在佛罗伦萨政府中地位的加强,这种以公共善为前提的有机合作主义又发展为一种平等观念,即所有行会在属于全体公民的政府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这种行会共和主义的极致便是梳毛工人起义建立起来的工人行会政府。
这样,早期的基于摆脱外来皇帝统治的“自由”便发展为宪法上的自由。正如布鲁尼(Leonardo Bruni,约1370~1444年)在《佛罗伦萨颂》(Panegyric to the City of Florence)中所说的那样,“涉及大多数人的事务,应该由全体公民按照法律程序作出决定。这样,在这座神圣的城市里,自由得到了发展,公正得到了保障。……这些人监督政府、主持正义、废立法律、保障平等。这样,佛罗伦萨人可以既享有自由,又受到约束”。也就是说,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可以保护穷人免受富人的欺压。布鲁尼写作《佛罗伦萨颂》的时候(1402~1403年),正是米兰战争刚刚结束,汉斯·巴伦(Hans Baron)所称的“市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在城中高涨的时候。从米兰战争到15世纪20年代,共和传统所宣扬的人的政治性得到了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意大利半岛上存在着的诸多君主国,也在宫廷中发展出了一种王权文化,与之并行的是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对于这些独裁者事实上的权威的认可。巴特鲁(Bartolus de Saxoferrato,1313~1357年)是其中一位代表,他认为意大利城邦事实上是自由的,因而“其自身就具有真正的主权”。在此前提之下,他区分了“具有法律资格”的暴君和“不具有法律资格”的暴君。根据他的标准,费拉拉(Ferrara)的终身总督埃斯特(Este)可以被称为合法的,而佛罗伦萨的罗伦佐·德·美第奇则被斥为暴君。
但是在佛罗伦萨城中,布鲁尼这样的市民人文主义者已经在美第奇的寡头专制之下改变了对共和自由和民众宪法的描述,将其规定为民主制和贵族制混合型的国家,承认了寡头对于立法的控制。他在1439年《论佛罗伦萨人的宪法》(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lorentines)中这样说道:“正如我们们已经说过的,因为(佛罗伦萨的)政治体制有一种混合性质,所以,其中的有些因素更倾向于民主制,而另外一些因素则更倾向于贵族制,这就很容易理解了。官员的任期都很短,这个规定是民主制的;……所有的事务都是预先商议过的,只有经过主要官员决定的事务才可以交给人民,这个规定是贵族制的。在我看来,贵族制的规定还包括,人民没有修订(法律)的权力,而只有赞成或否定的权力。”
到15世纪下半叶,随着美第奇统治的加强,佛罗伦萨的共和理论进一步削弱。布鲁尼的共和自由的宪法精神被巴尔托洛缪·斯卡拉(Bartolomeo Scala,1430~1497年)推翻了,他在1483年的《关于法律和审判的对话》(Dialogue on Laws and Judgments)中提出,善良而灵活的独裁者比不变的法律统治更可取 。这种所谓的“新共和主义”受到了当时在上层社会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影响。
到1530年共和国最终衰落的时候,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年)和维托里(Francesco Vettori,1474~1539年)都同意,共和与专制之间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了,而且也不能再说没有法律资格的独裁者就是暴君。维托里认为一切政府都是暴政,无论是法国、威尼斯还是佛罗伦萨 。1536年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在佛罗伦萨实行极权统治,圭恰迪尼便提出,“一切政治权力都源于暴力,没有什么合法权力”,可以看做他对当时现状的辩护,或者认可。马基雅维里在《论集》(The Discourses)中,也持这种看法。关于共和国的衰落,马基雅维里将其归结为一种“循环”。因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三种好的政府分别对应着暴君、寡头和放肆三种坏的政府,而共和国将在这六种政府当中不断地循环——一切共和国都始于君主制,君主变成暴君后贵族便起来反抗,贵族建立政权后又蜕化成寡头统治,平民便起来反抗,平民建立政权后又导致无政府状态,从而使他们相信还是回到最初的君主制为好。最终他把结论归结为命运:“一切共和国命中注定要经历这种循环。”
以上是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其共和政体所持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回顾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它的研究。
佛罗伦萨研究一直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学家们对此表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关注角度:有些侧重于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试图分析它在11世纪时尚且是一个小城镇,为什么到1300年时却已跻身于欧洲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列;有些对佛罗伦萨层出不穷的历史名人更为关注:但丁、薄伽丘;乔托、米开朗基罗;托钵僧萨伏那洛拉,家族统治者美第奇;萨卢塔蒂、布鲁尼;马基雅维里、圭恰迪尼……还有一些研究者的兴趣则集中在这个城市的政治发展历史上:自治公社的兴起、共和国的起落、君主国的建立,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佛罗伦萨历史的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阶段,按照坚尼·布鲁克尔(Gene Brucker)的说法,前工业时代没有哪个城市像佛罗伦萨这样被人们如此细致地研究过。
长久以来如此大规模的研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各国的学者们无论在研究主题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各有思路,如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却很少能对某一种方法或某些课题的优先性达成一致;同时,各家往往关注于自己的研究视野,较少参照、对比史学同行们的研究课题,或是他们对同类课题的研究思路。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这样一个宏大的研究范畴却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或更多的学术流派,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的交流和促进。
不过,虽然佛罗伦萨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缺乏明显的体系特征,但是也有一些特定的时期、特定的问题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比如说,“二战”前历史学家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佛罗伦萨在黑死病以后数十年间的情况,这些学者包括罗伯特·戴维逊(Robert Davidsohn)、加塔诺·萨尔韦米尼(Gaetano Salvemini)、尼古拉·奥托卡(Nicola Ottokar)、阿曼多·萨波里(Armando Sapori),以及多伦(Alfred Doren)和德·鲁维尔(Raymond de Roover)。戴维逊的四卷本《佛罗伦萨史(1896~1927年)》详尽考察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其中尤其注重对经济状况的记述和分析。多伦专门研究佛罗伦萨经济史,主要著作包括《13和14世纪佛罗伦萨行会的发展与组织》(1897年德文版)、《14至16世纪时期佛罗伦萨的毛织工业》(1901年德文版)以及《意大利经济史》(1934年德文版)。萨波里作为意大利经济史专家,除了出版相关专著,更挖掘整理了诸多史料,包括《皮鲁西家族账册》(1934年意大利文版)、《阿尔伯蒂家族帐册》(1952年意大利文版)等,成为后来学者展开研究的重要基础。而德·鲁维尔的重大贡献则在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缺少美第奇家族的银行账册,而他在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未被整理的大批文献中发现了美第奇银行的3本秘密账册,成为学界的重大事件。鲁维尔后来根据这批史料完成了他的著作《美第奇银行的兴衰》(1963年英文版)。
从14世纪中期到15世纪末期是史学家们关注的另一个时间段,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次“危机”上。第一次危机是在14世纪40年代,当时佛罗伦萨的发展突然被接踵而至的饥荒、瘟疫和经济混乱打断,因此人口统计学派和经济学派的史学家们对这一时期尤为关注。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5世纪初,这次危机也被史学家们看做是佛罗伦萨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转折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标志性的转变。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494年,当时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这一事件引发了佛罗伦萨乃至整个半岛的一系列变故。
然而,这种以“危机”为坐标系的分期方法并没有在佛罗伦萨研究者当中达成普遍共识。在是否认同这种分期的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彼此截然对立的学术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戴维·赫利希(David Herlihy)和菲利普·琼斯(Philip Jones)。这两个人都是研究中世纪晚期托斯卡纳地区(Tuscany)经济史的专家。赫利希强调托斯卡那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转折点和分期,他认为,14世纪40年代的人口骤减构成了这一地区历史上的一个危机时期,它标志着3个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经济停滞期和复苏期。他强调危机之前的古老土地贵族政权与之后中产阶级建立起的新秩序之间的区别,认为文艺复兴标志着佛罗伦萨(和托斯卡那)历史上的一个全新时期。
琼斯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托斯卡那农业史,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作了分析,认为托斯卡那地区中世纪庄园的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并没有明确的、决定性的断裂点和转折点。也就是说,相比于赫利希,琼斯更强调这一地区中世纪土地制度在历史中的延续性、多样性和多变性,而弱化了城镇中产阶级对于解决农村若干弊病的救治作用。 基于此,琼斯甚至对文艺复兴的概念表示了怀疑,他在一篇研究政治制度的论文中提出,11~18世纪,托斯卡那地区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观点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国家’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应该禁止在书中使用”。
大部分研究者不同意琼斯这个大胆的论断,因为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德尼斯·海(Denys Hay)的一句话代表了他们的共同观点:“文艺复兴确实存在过。” 不过同时他又提出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数不胜数”,这就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了。事实上,认可文艺复兴概念的学者们在若干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例如,如何界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是否应该将它们的定义和佛罗伦萨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等等。乔治·霍姆斯(George Holmes)认为文艺复兴是佛罗伦萨的发明和创造,是一场思想运动,“它以极端和突然的方式实现了思想的世俗化,并得到了各种上层力量的支持,影响了范围广泛的利益群体,……它使得一些极具原创性的观念经过一场很短暂的运动便迅速开花结果”。对于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或政治史的学者来说,这种转变并不像霍姆斯所说的那么突然,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是他们也同意,从14世纪到15世纪,佛罗伦萨的物质环境和思想意识领域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自由说。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人物是瑞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西斯蒙蒂(J. C. L. S. de Sismondi),在他看来,历史包含着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和热情,人们“探索历史”,也应该是为了得到“人类政治管理的教育”,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历史中包含着道德教育,它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重要性”。西斯蒙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他认为,“从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那一刻起——为公共善而建立这个政府,他们就已经成功了:当别的民族还在受磨难的时候,他们在智慧和美德中崛起了”。因为“每个佛罗伦萨人,即使他贫穷、被忽视,而且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做着手工劳动,他都能感觉到自己是祖国的一分子”。基于这种观点,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对公社政府都怀着肯定和赞美的态度,对美第奇政府则持贬抑态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