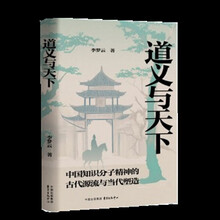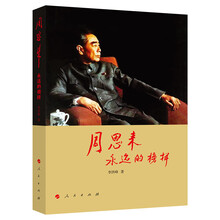要认识香港人这个特殊品种,不能不追溯历史。1997年前的100多年间,香港一直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在这方面,香港人其实一点也不独特,与其他前英国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加纳、尼日利亚、巴勒斯坦等)的人民一样,经历了被殖民化的洗礼。英国的殖民化就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今日有些香港人声称要“去大陆化”,并无新意,只不过是英国人进行殖民化的延续,甚至是英国人殖民化努力的成果。
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多如牛毛,都徘徊在民族主义者对前帝国殖民的批判和帝国主义者对殖民扩张的辩解之间;值得留意而且必须分析但又往往被忽略的一个现象却是前被殖民者在后殖民时期对殖民主义的辩解。
这个被忽略的现象亦有迹可寻。由于当前政治论述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的前殖民者手上,在主流的论述之中,民族主义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贬义,逐渐被等同为一种极端的政治行为。比如在钓鱼岛群的争端中,日本右翼游行反华、呼吁日本政府武力夺岛、向中国驻日使馆寄子弹、日本自卫队向正规军转型等,掌握舆论权的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评论日本时一律禁用“民族主义”这个措辞,因为日本是北约(西方)的盟友,但当中国人进行反日活动时,西方主流传媒却从不吝啬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民族主义逐渐失控的社会。在国际新闻语言的脉络中,“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操控国际政治环境的一个手段:在国际舆论上对某国或某组织定性、扣帽子,帽子一旦扣上,便无须论辩,更不用论证。除了“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手段的国际新闻语言帽子还包括“共产国家”、“不民主国家”、“狂人(卡扎菲)”、“流氓国家”、“恐怖主义组织”、“邪恶轴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拥有制造核武能力”等,日新月异,但都是新瓶旧酒。只要被贴上这些标签,西方国家便自动有权颠覆你的政府、侵略你的国家、屠杀你的平民,因为在西方主流传媒制造的舆论中,标签等同判刑,因此已无须论辩。
随着后现代文学理论的流行,很多来自前殖民宗主国的“学者”开始对殖民主义进行另类的论述。前殖民者说,不要以极端的民族主义来审视殖民主义,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见到殖民主义的一些优点。但殖民主义明明就是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个说法其实不十分妥当,因为这个表述方式误传一个讯息,就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站在平等的竞争立场。就正如强奸(或劫掠、欺凌)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殖民主义也不可以被歪曲为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用现代社会心理学语言表述,殖民主义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欺凌,不同的只是场景和规模的变异:欺凌行为不是小规模地发生在家庭内或操场上,而是大规模地在人家的土地上对人家的伤害(经济、文化、心理、生理、宗教、精神等方面)。这种欺凌行为的后果不会因欺凌行为的终结而终结,对受害国来说,被盗取的有限资源一去不复返,更严重的是受害者的心理创伤,此所以很多被酗酒父母虐待的儿童终生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当今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说他们祖先的帝国主义扩张及殖民已经是遥远的历史,前被殖民国不要将今日的贫穷或政治动荡归咎于帝国的儿子们,那是因为帝国的儿子们从来不是受害者,而且一直是以继承过来的欺凌者身份发言。
这或许解释了前殖民宗主国的“学者”对殖民主义的新辩解。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被殖民者会为殖民者辩解呢?
这是相当发人深省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模拟——被强奸者(或被劫掠者、被欺凌者)为强奸者(或盗匪、欺凌者)辩解,是否需要深究?固然,被强奸者可以爱上强奸她的人;被劫掠者可以庆幸盗匪没有拿走被劫掠者手上的最后一分钱;被欺凌者可以感激欺凌者手下留情,没有将受害人的双手双脚都打断了。诸如此类的感性原因,都是剑走偏锋的理由,只能解释为例外,不能解释为超越地域人种的一个普遍现象。今年(2012),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和毕业于牛津的民运斗士昂山素季以缅甸国会议员的身份出访欧洲和美国,不用自己民族语言赋予的名字“Myanmar”来谈说缅甸,却用前宗主国英国给缅甸起的名字“Burma”来称呼自己的国家,是心理上怀恋殖民统治的典型。香港的“民主精英”也不乏对前殖民宗主国的怀恋。1988年,同样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和毕业于英国律师学院的李柱铭访问美国时便声称“如果香港继续受一百年英国的殖民统治,我想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但现在香港要回归中国”(1988年4月8日《信报》)。殖民教育的去民族化心智操控力量显然难以低估。
已经移民美国的孔诰烽先生,在当地的大学任职社会学副教授,写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发表于2005年7月11日的《明报》,题为“殖民时代时光再临的期待”,是脑袋被殖民的病态呈现,“出类拔萃”。孔先生说“韩国在民主化与经济再起飞后,民族自信心大增,学术界最近掀起了再思韩国殖民经验的热潮”,然后又说由“十多位中、韩、美学者参与的Colonial Modernity of Korea(199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是这一学术思潮的结晶,而这一学术思潮的结晶肯定了殖民经验(但不等同歌功颂德),认为视角崭新,随即得出一个结论:“当可为我们再思香港的殖民经验提供有力参考”云云。首先,孔先生起码有三个地方搞错了或严重误导。一,书名不是Colonial Modernity of Korea,而是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韩国的殖民地现代性》)。二,所谓的“十多位中、韩、美学者”是意图制造客观假象的误导,因为韩裔学者只占六位,而六位韩裔学者之中只有韩国中央研究院的韩道贤教授和庆尚大学的金仲燮教授为韩国人,所有作者都是美国人(包括两名中国裔的学者),即美国学者,所以是美国学者的观点,不能代表韩国学术界的意见。三,“韩国在民主化与经济再起飞后,民族自信心大增……”属严重的时序误导,因此让读者以为韩国先民主化,后经济起飞,后民族自信心大增。
最后一点必须澄清。事实绝非“追求民主理想”的孔先生一厢情愿但与历史相违的春秋笔法。1961年,陆军军官朴正熙策划政变,成功后以“平民”身份连续三届“当选”总统。朴正熙实践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计划经济),并且宣称目标对准1981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要达到1 000美元,被嘲痴人说梦。1973年,朴正熙开展有名的“重化工业化”项目。1972—1979年间,韩国人民的人均国民收入飞跃五倍以上。1977年,韩国人民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 000美元,比预期早了四年!在同一期间,韩国出口更厉害,增加了九倍。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事实。不愿查找文献档案的懒惰“学者”可以花899英镑买一本张夏准的Bad Samaritans—The Guilty Secrets of Rich Nations & the Threat to Global Prosperity来翻阅。该书序言引韩国现代经济建设史为例,证明新自由主义原则如自由市场和私有化及民主政制,恰恰都不是新自由主义者称颂的韩国经济起飞的原因。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一样。这些例子非常有力地告诉我们,历史上很多国家和社会都是先有经济起飞,建立了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才能不经社会动荡向“民主”过渡,这样的“民主”才会持久;而经济建设往往要在自觉而有理想的比较专制的政权下才能取得成功。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蒋中正和蒋经国统治下的台湾地区(“十大建设”不也是计划经济吗)、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都证明了这个历史“规律”。民族自信亦只能按这个历史规律依序出现。孔诰烽先生的“韩国在民主化与经济再起飞后,民族自信心大增……”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描述,否则便是非常不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写作风格,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韩国先有民主化,才有经济起飞,即误以为民主化是经济起飞的条件或前因。
孔诰烽先生的论述不单有不诚实之嫌,其论点亦流于简单且表面,虽然他声称“‘殖民主义’VS‘民族解放’”的论述框架太简单化:“作者认为,日本殖民主义除了为韩国带来残酷压迫,亦带来了现代化。殖民者推动现代化,当然是为了一己利益,但当现代化打开的新空间遇上本土不满现状的暗涌时,却会导致反殖意识的形成。殖民者为回应下层反抗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加上由殖民地母国传来的激进思想,又会成为进一步推动反抗运动的催化剂。”这种表面化和无耻的思考方式,出自一名学者之口,实在非常混账:(意图)强奸者为了顺利强奸,拳脚相向之外,还对受害人甜言蜜语;但当甜言蜜语打开新的空间(受害人以为还有一线生机),反而鼓励了受害人的反抗意识;强奸者为了响应受害人的反抗,匆匆进行了强奸,没有享受太多,但受害人经过这段强奸经验,对走夜路和与男性交往便更小心了、更“现代”了。
孔诰烽先生其实是说,殖民主义为殖民地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亦为殖民地带来一些好的东西;但殖民主义导致反殖民意识的形成,殖民者为了回应反抗而采取改革措施;殖民地宗主国传来的激进思想又成为推动反抗运动的催化剂。我不了解孔先生读了多少关于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论著,但据我自己的观察,从民族主义出发的论述很少将殖民者带来的“好东西”一笔抹杀。民族主义批判(下称“民论”)通常提出一个警惕,那些“好东西”都是有条件的,属于统治工具。这样的论述简单化了历史事实吗?恰恰没有。反过来,孔先生依附的新见解(下称“殖论”)说,殖民主义的确带来不好的东西(而且已经说得太多了,所以可略了),但它的确有带来一些“好东西”,尽管这些“好东西”都为了一己(殖民者)的利益。这便很有狡辩的味道了。让我们将两种思辨方式做个对比。
民论说:殖民主义带来不好的东西A,也带来“好”的东西B,而“好东西”应该理解为R。
殖论说:民论说殖民主义带来不好的东西A,也带来好的东西B,而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很明显,民论没有简化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简化殖民主义论述的是殖论。民论认为B的“好”不能理解为正常意义下的“好”,因此有必要加上引号以示警惕;殖论认为无须加引号,好就是好。按这种畸形的论调,引而申之,强奸犯的辩护律师大可采用如下寻求减刑的辩护手段:虽然强奸在肉体上和心理上伤害了受害人,但受害人因此怀孕了,而且据说是个男丁,所以强奸增加了受害人一家的人口,而且增加的是劳动人口,因此能增加受害人一家的收入。假如孔诰烽先生是陪审员或法官,你会接受上述求减刑的辩护吗?又或者假如受害人是你的女儿或妻子,你还会那么开通地用辩护律师的(也就是阁下的)“崭新视角”理解强奸行为吗?孔先生会期待“强奸时代美好时光的再临”吗?如果强奸犯的辩护律师的论理无耻,孔先生的“肯定殖民经验”高论是否同样“礼义廉”?
韩国外国语大学的赵荣汉教授以韩国人/被殖民者的观点批评了《韩国的殖民地现代性》,指出一方面韩国学界普遍地不信任美国学界,认为美国学界态度傲慢,“另一方面,美国学界则倾向于将韩国学界简化为民族主义措辞的喉舌,韩国学界自然觉得受辱。这个徒然的循环本质上源于全球学界的等级结构。韩国学界不能像美国学界般发声,甚至缺乏向美国学界投诉的工具。有关韩国作为殖民地的过去,韩国在这方面的连续研究反倒更多呈现韩国学界被殖民的幅度这样的一个学术现状……”“Cho Younghan:Colonial Mordernity Matters?”,Cultural Studies,Issue 5(Special Issue:Colonial Modernity and Beyond:The East Asian Context),2012,661
所谓的“殖民地现代性”,韩国学界和西方学者各有不同的诠释。赵荣汉的文章引述了另一名韩国学者的意见——李延在《历史的空间》(2010)一书中批评了西方学者那种隔岸观火的学究态度:
对西方的‘评审性’史料编纂者来说,他们可以在一个距离之外观察殖民地的情况,因此能将作为一个控制殖民地的同化或日本化政策视为能产生一种模仿的技巧,能导致各种反应或甚至看似被殖民者(韩国人)的反抗活动。但对经历殖民占领过程的人来说,日本化政策不能诠释为一个反抗的符号。Ibid,656657.
这便很清楚了。孔诰烽先生的“韩国……学术界最近掀起了再思韩国殖民经验的热潮”,而《韩国的殖民地现代性》是这一学术思潮的结晶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韩国的殖民地现代性》指出的只是一个美国观点,而且普遍地不为韩国学者信任!原因不辩自明。拥有殖民者身份的美国学者不能代表被殖民者(韩国人)发言。但问题正如赵荣汉教授低调地指出,由(前)殖民者建立的今日的世界,话语权掌握在(前)殖民者的手上,在现时全球学界的等级结构中,(前)被殖民者还没有具备平等的话语权。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为什么香港的大学教授们那么热衷写英语论文,“乞求”英美学刊发表他们的文章,因为掌握学术话语权的是说英语的(前)殖民者,香港的大学教授们的论文恰恰就是写给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学者看的!还有什么比这个现象更能道出个中奥妙吗?
因此,孔诰烽先生的“当可为我们再思香港的殖民经验提供有力参考”的“韩国经验”根本就不是韩国经验,而是掌握学术话语权的美国学界眼中的“韩国经验”。换句话说,要我们听从掌握学术话语权的美国学界的某些意见或观点罢了。可惜的是,韩国学者已经普遍地不信任或不同意美国学界关于殖民主义的意见,孔诰烽先生何苦要香港人学习美国学界眼中的“韩国经验”呢?
显然,孔诰烽先生认为美国学者说了算数,他们有下定论的最终权力(因为他们是掌握话语权的前殖民者)。于是,孔先生将他所谓的“韩国经验”应用在香港身上:
反观香港,战后的亲北京左派,一直强调港英统治的腐败黑暗。今天不少带北京观点的香港史书籍,虽然承认香港社会在70年代开始不断进步,但它们大都将此归因于整体经济增长与华人资本家的崛起,而小心翼翼地避免将功劳归于港英政府或左派系统外的民间抗争。
事实上,70年代之所以能够成为香港殖民时代的黄金十年,并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有赖当时殖民政府与本地社会建立的新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
孔诰烽先生的思路不断印证了我们的观察。在上面援引的文字中,香港的“进步”、“黄金十年”、“新社会契约”的用法,不论在语法上或修辞上,都不加引号。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这就是孔先生肤浅的崭新视角。作为一个殖民统治地区的“进步”有怎样的内容和政治含义?为什么香港的“黄金十年”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即在英国统治了香港达一个世纪之后,殖民统治的末期才出现,而不在殖民统治的早期或中期?所谓的“新社会契约”是个准确的表述吗?请问中国在枪口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与英国的“契约”吗?请问被强奸者答应不反抗以求最少伤害是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契约”吗?同理,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契约”吗?如果是的话,恐怕“社会契约”的概念早已虚浮得失去任何作为认知工具的价值了。所谓殖民政府与香港本地社会建立“新社会契约”完全是孔诰烽先生的虚构。还记得前香港市政局主席(1973—1981)沙利士的自述吗?香港市政局会议厅主席位藏有一个按钮,用来关掉耳机,即掌握听与不听的权力。这样的权力结构能称为一种“社会契约”吗,能产生“社会契约”吗?
上世纪70年代的所谓“黄金十年”是一个历史偶然。
殖民时代香港的贪污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六七十年代。香港贪污成风的主因有两个,与殖民统治密不可分。
第一个原因是特殊的权力结构。在《香港画像》一文,我分析了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社会的统治结构,这里长话短说。英国殖民政府优越的统治模式是宗主国(即孔诰烽先生口中的“殖民统治的母国”)没有直接“统治”当地社会,因此不会弄脏手脚。比如1966年的天星小轮加价引起的暴动事件,青年苏守忠在中环爱丁堡广场码头绝食抗议,其后一生被香港政治部打压(这些肮脏的工作都是由香港的二等公民统治精英执行的!),困境度日,转工70多次,最后剃度出家。有人将今日替“泛民”摇旗呐喊的年轻人视为继承了苏守忠的叛逆,真是莫大的误解。苏守忠对抗的是殖民统治,并且承受了殖民统治地区二等公民的迫害,他的脊梁是直的;今日的年轻人是抱着对殖民统治者的怀恋心情抗拒融入原民族,驼背而不自知!英国殖民政府在殖民统治地区培养少数的当地“精英”,使他们成为殖民统治地区的二等公民,替实际的统治者(英国人)管治当地非二等公民的人民,后者顺理成章成为殖民统治地区统治结构的最底层——三等公民。二等公民之中亦有等级的划分。能说流利英语的晋身行政局、立法局,公务员系统的头头低一级,而公务员普遍地沦为二等公民的底层。这个层叠式的统治结构造成一个现象:办事要找中间人。比如为了摆个地摊、申请一张执照或请某机关尽快批准某个项目,三等公民便自然地要向二等公民买个方便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为方便殖民者统治的殖民教育。这一点已有论者分析过,并不新鲜。一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香港人口达300万人,大学只有一所,这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惯例。虽然大学只有一所,职业训练学校和课程却颇多,目的当然是确保香港的就业人口,另一方面则要控制难免涉及社会、政治和道德理论的人文学科。由于学位严重不足(我强调“严重”两字),形成了香港学生出境留学的潮流,其中一部分的香港学生则到台湾念大学。那个年代,入读香港大学的机会掌握在几所教会办的贵族学校手中。几百万的人口,每年念政治科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艺术理论和文学的毕业生只有极少数(可能只有两三百人)。事实上,香港大学1961年的学生总人数为2 000;1967年前,香港大学没有社会科学学系;法律系到1969年才成立。由于只有一所大学,人文学科毕业生几乎没有机会在本地深造及成为学者。这就是香港被称为“文化沙漠”的主要原因,亦造成整个社会缺乏人文学科的素养。结果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唯利是图,没有文化素养,缺乏思考能力的香港人。反观台湾,五六十年代酿出乡土文学,造就了一批出色的文学家;80年代又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新生代电影。“自信心”(英语应该叫作“inferiority complex”)爆棚的香港人活在流行文化的瓮中,以追赶欧美潮流为社会导向,因此所谓的“四大才子”都是流行文化的写手;但有趣的是,在没有文化的摩登市集中,香港的“才子”、“才女”比所有华人社会都多。因此,香港只能产生比较大众化的电影和Cantopop 是可以理解的;电影主题以城市喜剧小品居多,之后便是武打片和喜剧的天下了,而音乐主题当然离不开伤风悲秋的情榻之事。结果显然出不了殖民政府的意料之外,香港没有文学思潮、没有社会理论、没有政治理论、没有哲学理论,只有几位源自内地的新儒家学者默默地耕耘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但总不及基督教会建立的教堂和学校多和快。
这两个主因使香港成为贪污的天堂。所以就某程度而言,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贪污是结构性的。到了六七十年代,贪污(包括臭名远播的香港皇家警队)造成严重的管治危机,才有反贪污的政策出台,但出台的不单是廉政公署。
六七十年代,内地的“文革”帮忙制造出孔诰烽先生口中的“黄金十年”。简单地说,革命思潮从内地涌入香港。殖民统治地区的贪赃枉法、贫富分化、恶劣的居住环境来自香港前宗主国的煽情小报《每日邮报》在2012年1月11日报道香港“笼民”的困难,美国的假自由派《赫芬顿邮报》(2012年1月12日)改个标题后便帮忙广传开去,仿佛“笼民”问题源于香港回归后的管理不善。欠缺专业素养的记者没有说或根本无知的是,“笼民”早在港英时代便出现,是前殖民者操控“官地”买卖,抬高地价造成的恶果!等为殖民统治带来直接冲击,聪明的英国人比香港人更明白这个隐忧。此所以1973年成立了香港房屋委员会,大量建造公共屋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肃清二等公民和三等公民之间的贪污行为。后者对香港从制造业向金融业和旅游业转型功不可没。当然还有“清洁运动”(也是70年代)等由殖民政府推展的社会政策,就是害怕“文革”工人阶级的造反思潮随着殖民统治地区社会的腐败和不公平而传入香港,动摇香港的殖民统治。事实上,六七暴动的确动摇了英国统治香港的决心。上述的那些政策都是从上而下的,都是为了巩固殖民政府的统治态势;用今日的语言来说,就是维稳!什么“社会契约”?《殖民时代时光再临的期待》一文中描绘的香港历史只是作者脑袋中的虚构,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
本文用孔诰烽先生做例子是因为他的文章体现了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一个现象: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被殖民者会为殖民者辩解?为什么孔诰烽、李柱铭及一众“泛民”对他们的前殖民统治的“母国”依依不舍?这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殖民主义就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去民族化的首要任务就是让被殖民者与原属民族/国家产生疏离感,而使被殖民者与原属民族/国家产生疏离感的根本手段显然是让两者说不同的语言。关于这点,香港的殖民政府做到了。一直到80年代,除了在内地出生的移民,香港人基本上不懂国语或普通话。另一个手段是制造不懂思考的人口。关于这点,殖民教育制度是一张保单,香港的殖民政府亦做到了。因而,香港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简单概括:香港是一个从有限度的轻工业和转口商业向旅游业和金融业转型的买办社会(秋瑾使用的意义);在殖民政府控制下,香港的整个社会动力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向上爬;过去是文化沙漠,今日仍然逐水草而居,只有潮流,没有根干;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学术界,以一种欠缺历史的方式依存在宗主国的文化阴影之下,亦仅止于文化阴影之下。
我们想要探讨的是这个“依存”的性质和政治含义。当代政治论述的最大问题是抽象化和物化论述对象,因此走了很多岔路,似是而非,未能一击即中,故能容许“殖民时代时光再临的期待”或“韩国的殖民地现代性”一类诡辩渗透公共意识。本文书写至今,其实已经暗示了一个论述方向:用社会心理学的语言来分析殖民主义,或许是时候了。尤其是当我们越来越多使用“国际社会”的措辞时,殖民主义的“霸凌”(bullying)和虐待(abuse)本质变得越加明显。
殖民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霸凌”和虐待行为,而这类行为是在长期绑架(abduction)的过程中进行的。不正确地理解或抽象地理解殖民主义的性质,不能解释前被殖民者对前殖民者的维护心理。在社会心理学的圈子和众多教师的经验中,诋毁、推踢、夺取人家所有、恐吓、威胁、强迫人家做不愿做的事等普遍都被界定为“霸凌”行为。比如,Michael JBoulton,“Teacher珡 Views on Bullying:Definitions,Attitudes and Ability to Cope,”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67(1997),223233。在欧美各国的殖民史中,不难找到相对应的殖民政策及行为。“霸凌”行为有一个特征,就是通常是以组群的方式攻击个体。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列强意图瓜分中国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香港也是这时被割让及“租借”给英国的。近的有北约国家入侵和肢解前南联盟及北约国家推翻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今日在我们眼前操演的是北约国家对叙利亚的“霸凌”。同时,被攻击或“霸凌”的个体必须呈现软弱的状态,因此在武力或威胁之下才有被迫顺从的可能性。为了能够支配受害者,整个“霸凌”过程必须靠权力的不断重复演示来维持。历史上每一个殖民统治地区的独立,都源于殖民者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没有能力重复演示其权力,因此失去了支配的地位。香港的回归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规律,但必须认识清楚的是,英国政府没有能力在香港重复演示其权力的原因不是香港人出现民族意识醒觉或香港人发现其主体意识而进行反抗。在殖民时代,作为一个由买办操作的市集,香港从来不是一个叛逆性社会。英国政府没有能力在香港重复演示其权力的真正原因是香港归属的民族/国家在殖民统治地区的背后移动了权力的天平。
但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在绑架状态之下的长期“霸凌”和虐待,造成了被殖民者严重的心理创伤。殖民化系统的推行一方面将殖民者的语言文化宗教提升到被统治阶层认可的位置,另一方面则将被殖民者的族语(国语/普通话)抹去,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用殖民者认可的世界历史来对抗被殖民者认可的中国历史,将本土文化局限在通俗文化的领域。在今日的香港,西方等同开放,中国等同专制,西方领导潮流、独领风骚,这都印证了殖民化系统的洗脑能力。香港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就是这样失去的。
1973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发生一起银行劫案,两名劫匪劫持银行职员六日,充作谈判人质。在事件中,人质表现出对劫匪存在情绪依赖。事后,人质公开维护劫匪,为劫匪辩解。瑞典犯罪心理学家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听来新潮、专业,但名称背后的心理症状并不新鲜。它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应对机制(coping mechanism),又称为“生存鉴定综合征”、“常识性综合征”或“转移”。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特别行动及研究单位的德维恩·菲尤斯利尔博士研究所得,这种心理应对机制包括三个可单发可并发的要素:一,人质对权力当局产生负面情绪;二,人质对劫持人质者产生正面情绪;三,劫持人质者以正面情绪回报人质的正面情绪。DGwadyne Fuselier,“Placing the Stockholm Syndrome in Perspective,”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Vol88,No7(July 1999),2225:http://www曠戀椀柠漀瘀/stats珠攀爀瘀椀挀攀猀/publications/law无渀昀漀爀挀攀洀攀渀琀拠甀氀氀攀琀椀渀/1999烠搀昀猀/jul99leb.pdf.
放在殖民统治后期和后殖民时代的香港,上述用来鉴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三个要素不约而同地并发,绝非巧合。首先,“泛民”对权力当局产生负面情绪是明确的。权力当局就是中国大陆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特区政府。所谓的“共产党”、“民主”、“人权”等都是说词,可以是真确,但不必要是真确,因为无可否认的根本是“泛民”不喜欢中国大陆,即“去大陆化”背后的心理症结。第二,“泛民”对英国政府产生正面情绪亦明显不过。李柱铭心愿英国继续殖民香港百年已是港人耳熟能详的名句,以“汉奸”自诩亦已成“壮举”。孔诰烽对殖民时代时光再临的期待更是“名正言顺”了。第三,英国政府和其他的前殖民国(即北约的主要成员国,亦即G8成员国,巧合地亦几乎就是当年联军抢掠北京城的八国的翻版!)对“泛民”优遇有加,甚至在背后做策略(和财务)支持,对此“维基泄密”已有证实。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质与设障系统(HOBAS)——一个覆盖全美国各州共1 200多宗人质和设障事件的国家数据库显示,92%的事件受害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方面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换句话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颇为罕见,发生率大概为8%。英语维基有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词条说的27%(读取日期:2012年10月 12 日)是错的。这8%再次巧合地吻合香港的情况。2010年的香港人口约为7 000 000人,7 000 000×0ム8=560 000人,即香港人中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最大数目是560 000人。现取用香港最大型的示威游行为例,港大民研的数字为约500 000人参见香港大学民意网站,http://hkupop棠欀甀棠欀/chinese/columns/columns105.html。读取日期:2012年10月12日。,略低于8%的560 000人,非常接近HOBAS的分析数字。后殖民时代出生的香港新一代,没有经过殖民统治的劫持,因此免除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可能性。两个现象证明了这个分析:一,近年的七一游行人数已经下滑到30 000人左右(约为香港人口的043%);二,近两届的立法会选举中,“泛民”获得的票数和议席开始呈现减缩的趋势。
但同一个研究显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出现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劫持事件跨越长时间;二,人质与劫持者保持接触;三,劫持者必须善待人质或起码没有使用肢体或语言暴力。放在殖民统治后期和后殖民时代的香港,上述三个条件亦巧合地满足了。百年的殖民史毫无疑问满足了第一个条件。第二和第三个条件需要一点解释。前面已经提到过,英国统治香港的手段是层叠式的,实际执行统治(三等公民)工作的是二等公民。二等公民就是香港的精英,长期以来,他们亦是殖民统治地区的既得利益者。由于二等公民(比如胡百全、简悦强、邓莲如、钟士元、李鹏飞、陈方安生等)是实际统治的执行者,却非决策者,而是听命者,因此与英国统治阶层必然有持续性的接触。这满足了第二个条件。由于要靠二等公民执行实际的统治工作,英政府亦聪明地对二等公民相当礼遇,封侯拜爵便是笼络手法之一,因此胡百全、简悦强、邓莲如、钟士元、李鹏飞、陈方安生等都挂有大英帝国的勋章!这满足了第三个条件。港英时期的“太平绅士”授衔就是培养管治三等公民的二等公民的一个手段;“御用大律师”(Queen珡 Counsel,即为女王服务的法律顾问)的册封是另一个笼络手段。比如李柱铭便是为女王服务的御用大律师兼太平绅士。
假如上述的分析正确或接近历史现实,殖民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绑架/劫持。在这个绑架/劫持的过程中,殖民主义的内容根本就是一种“霸凌”和虐待行为比如夺取殖民地的资源。要知道,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力资源需要好几代的栽培,科技发展则以百年为单位,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伤害既深且远。,但英国的层叠式统治手段跃过二等公民,直接的统治对象是三等公民(普罗大众);也就是说,殖民主义的“霸凌”和虐待行为的直接受害人是三等公民(比如苏守忠),作为殖民统治地区管治精英的二等公民反而是受优遇的既得利益者。不理解这段殖民历史的核心性质,便不能解释太多的后殖民现象。仅仅将陈方安生之流贴标签为“港英余孽”或将李柱铭骂为“汉奸”,显然是还没有摸清殖民主义的性质和殖民主义的历史。用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今日香港的“泛民”对前大英帝国的依恋来自一种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上的应对机制。
这个分析同时解释了“泛民”思考能力严重低下或拒绝面对现实的现象,也就是面对负面事实而拒绝接受应有的结论。比如西方的所谓民主大国英国和美国政府有这样的一段历史——1953年,英美两国合谋推翻伊朗的民选政府,将首相摩萨台软禁至死,扶植独裁的伊朗王朝;美军在越战时使用化学武器;美军在越战时越境地毯式轰炸柬埔寨达数年之久,十几万柬埔寨平民被杀;1970年代,美国政府推翻智利的民选政府,谋杀总统阿连德,扶植建立皮诺切军特政府;1990年代,美国和法国推翻海地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扶植一个亲美国政府及财团的军政府;2003年,美国和西欧各国诬捏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侵略伊拉克等。这些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泛民”无动于衷,依然紧紧地拥抱着这些“民主”的前殖民者。没有什么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更能解释这个现象的了!
最后必须提出来的是,英国人的殖民化系统的中心是教育制度,这个制度的杰作是确保代殖民者管治香港的精英丧失民族感(去民族化)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洗脑)。今日“泛民”的表现及“港独”的嚣叫——重复没有经过脑袋思考过的口号,不在中国的大历史脉络中考虑问题,空喊从西方社会借来的“民主”、“人权”、“自由”、“一人一票”、“去大陆化”等口号——印证了上述观察。长期的去民族化和洗脑自然导致强烈的自卑感。香港人的自卑感对香港社会性格影响甚大,但内文有述,前言不赘。不妨稍作补充的是,“泛民”精英大多是基督教徒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月亮还是外国的圆!另一个实例来自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一窍不通但写了《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的挪威人钟祖康先生,写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要借故提醒读者他娶了一个白人(挪威人)老婆,作为一个黄种人,自卑到了极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