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父母权威的下降
自婴儿期就会被视为年轻的一代。每个孩子不仅能与人沟通,还能开始掌握公民资格对话必需的特殊话语;同样,在其“家族”群体建立起的复杂控制的帮助下,每个孩子还开始以文化规范之名义控制自己的攻击冲动。可是,这些共同的主题都无法公正处理教育差异产生的难以想象的多元化和广度:孩子们说每种语言,将无数种构成上一代生活传承的文化脚本付诸行动。孩子们参加测试、改变、修复、转化;父母们进行教育、调整、哄骗、命令。
命令——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假设没有一种初等教育能使任何一个五岁的孩子完美地社会化到对自己“父母”以原始培养之名义提出的要求永不反抗的程度。在这个或那个方面的反抗,是可以预期的。而且如果存在反抗的话,自由主义对话将会有一个新的转机。根据定义,初等教育的成功产物应能自己提出——即使是以犹豫不决且简单的方式——合法性问题:“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有对我颐指气使的权利?”
并且,根据合理性要求,问题一旦被提出,就必须得到答复。此外,质疑父母的合法性的行为开始使孩子获得参与为取得公民资格而进行的对话性测试。因此,从原则上讲,他的问题就不能用一种按中立性来说是不尊重孩子权利的答复被压制或被置之不理。如果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前辈从本质上就优于年轻公民,那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共同体是不能支持使用强迫手段的;也不能断然声称,父母必须比孩子自己更知道什么是对孩子有好处的。这些行为都明目张胆地违反了中立性原则。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孩子五岁以后还能说些什么来维护父母的权威呢?
34.1 控制
在公民资格一章里,我们已经提出需要对这个问题作出自由主义式答复的思想。回想一下那个费尽心思搜遍西海岸寻找陷入危险之人的有杀人倾向的离异者吧。见第19.4小节。尽管离异者在其他方面都能享受自由公民的待遇,但当指挥官为保护陷入危险之人包括肉体生存和物质存在的对话权利而对他强加特殊限制之时,他却不能有所怨言。对离异者行为的特殊限制并没有违背中立性原则;相反,它们是使其能够成为在与他人关系中享有中立性权利的公民的必要条件。
相同的基本原理亦可用来说明对孩子行为自由的限制。并不是说正常的五岁大的孩子就有能力将自己的杀人幻想付诸行动,可无论如何,孩子在五岁至青春期之间接受的教育,是影响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以何种方式处理日益增长的、可伤害他人的权力的重要因素。家庭内部文化规范不断潜移默化地强化可能降低孩子长大成人后主动违反刑法的几率。而如果这是真的,那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就必然面临一个让人费解的平衡:一方面,当一个年轻人迫不得已按教育者要求去做自己不想去做的事情时,这些特殊限制确实限制了年轻人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为处事的原始权利;另一方面,在童年时期设定特殊控制可能会提高年轻人免受刑法强加于有攻击性成年人的特殊限制的能力。简而言之,我们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套对公民一生都有用的行为限制,从而使强加于他身上的特殊限制的整体分量有可能降至最低。正如离异者无法抗议禁止他去西海岸的特殊限制规定,晚辈也不能抗议童年时期受到的特殊限制,这些特殊限制使他摆脱了之后生活中的大部分限制条件。根据中立性原则,这些限制不是违背了后辈的公民资格权利,而是他一生享有对话权利能得到最大认同的必要条件。
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刑法和自由主义家庭法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假设由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原因,规制对象为具有攻击性的成年人的刑法,是按照传统自由主义方法建构的,要求在强行限制自由之前,必须提供证明实际恶意行为的最高水平证据。见第19.6小节。这样引出的结论是,如果整体攻击性水平一直保持在可容忍的次优范围内,那么在婴儿期和童年期,对孩子“控制”管理之微妙形式的限制将沉重不堪。我说这些的时候,并非想表明我们应改变权衡刑法和家庭法的基本要求,以使得政策更易于限制成年人而父母却更难约束孩子。最关键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成年人以具有道德优势为借口管理孩子是不合法的。相反,父母控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限制性较少的手段,以使孩子长大成人后摆脱刑法会强加的更多侵入性限制。
然而,说明一个原则是一回事,弄清楚特定制度背景中合法的父母控制的特定形态,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不同的自由主义国家就父母控制的合法范围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仅很多相关因素会被质疑,而且不同的自由主义对比较加诸于父母和各种类型监管人身上的整体限制水平也会各持己见。解决善意分歧的方法,是第九章将提出的自由民主理论的主题。目前,假设政治讨论最终得出结论证明,孩子在五岁至十六岁(比如说)期间受到某些形式的父母控制是合理的,已经足够了。给定以上结论的话,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在漫长的限制期间内,父母控制应以何种方式逐步演进。
正是在此处出现了一个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父母越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控制功能,持续不断地将他们自身的善的概念强加于自己孩子身上的合法性就越少。暂且先不管弥漫着的悖论,这个结论可由父母控制原理直接推断而来。父母获得控制权,因为孩子如果要以一种避开刑法约束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攻击性行为,那就必须将自律习惯内在化。结果就是,当孩子成功将初等文化强加于他的基本控制内在化的时候,父母不可以认为取得了初步胜利,而把以更为详尽的形式将他们偏好的习惯强加于孩子之上视为合理的。一种自由主义教育,不是园艺学的一种高级形式,不是父母将年轻的幼苗修修剪剪从而形成他们自己想要的式样。在一种成功的自由主义教育中,孩子八岁时的抗争应比其四岁时的抗争更受到认真对待;而十二岁时的抗争,就应比八岁时更受到认真对待。
同构论证可引出第二个悖论:父母越没能成功地实现他们的控制功能,持续不断地对孩子行使父母权威的合法性就越多。但是在这一点上,论证转向了不同的方向。这很难得出以下结论:把初等教育义务搞砸了的人应在中等教育时期完成补救任务。而且,再一次地,必须慎重行使把孩子从原始家庭带走的权力,而这基于两层考虑:一是对暴政无可非议的恐惧,二是把孩子从原始环境带走本身就会破坏孩子处理自己攻击性能力的公认观点。
34.2 引导
当控制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式微,第二个原理——我称之为“引导”——开始独具分量。尽管控制和引导在现实生活中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我在探讨为合法的引导提供概念时会先忽略这个事实。
那么,假设把父母控制的限制合理度的决定权交到孩子手上,由他自己定夺是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棒球队员。再进一步假设年轻人确实想在美国少年棒球联赛中出类拔萃;可他发现很难面对这样的事实:要成为棒球大师必须付出的必不可少的代价,就是得接受大量枯燥无味的训练。正是在这一点上,熟悉孩子的成年人又能施以援手了。意识到孩子在比较达成目的方法的审慎判断方面经验不足,父母可能会找出方法向孩子说明(即使加进了他们自己的主张),他可能错误估计了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会涉及的代价或好处。最显而易见的是,孩子可能是简单实证错误的受害者:也许他认为一旦学会击中球,将来就能掌控在空中飞行的所有其他目标。而一旦打消了这个错误的念头,年轻人可能会转变心意,觉得弹钢琴比打球更好。
不那么显而易见但确实很重要的是,孩子会看错家庭之外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一个孩子倾向于假设“家庭”之外的世人会以他熟悉的基本文化模式对待他。此类假设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是很危险的。尽管公民拥有尊重爱护同胞的自由,但也拥有漠不关心,甚至看不起其他人生活方式的自由。再一次,在认识孩子的行为方面,只有建立在对更广大世界中人们的想法和动机进行非现实假设的基础上,父母通常处于最佳位置(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主张范围内)才讲得通。
然而,这些特别的引导权力的合法性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衰落——尽管与控制权衰退方式完全不同。当孩子拥有更多比较达到目的方式的经验,更多有关家庭之外的世界的经验,就会越来越难以想象他与父母的意见分歧是建立在轻率的基础之上;持续的争论将越来越表现为青年对家庭的理想产生异议,以及父母使用引导的权力来掩盖他们不合法的控制欲望。
35. 中等教育:自由主义原则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试着确定了父母能压制孩子之反抗的权力范围。可是,还存在第二种看待对抗的角度:孩子的角度。既然我们已经说明父母对压制孩子的异议权利主张逐渐势弱,那么与失望的父母亲相比,一种完整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必须以更具同情心的态度看待孩子的“不听话”。
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很明显,父母的命令让他有些烦恼。在明确表达是什么让他烦恼的过程中,他仍然会经历预料之中的困难。毕竟,他全部的“初等”教育都来自于父母及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根据假设,他们一直在告诉孩子,说他是个“坏孩子”。可是,孩子有权利知道在自由社会里,他的父母对事情的看法并非不容置疑吗?父母有权利阻止其他试图劝说孩子的其他人吗?那些人想让孩子知道自己的反抗并不是一种罪恶的标记,而是包含一种拥有比父母给他的更好生活的希望。
假设某些成年公民——高贵者——从孩子出生时就开始观察特定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可是,在孩子“初等”教育期间,高贵者与婴儿之间的所有交流都被切断,因为父母认为他的影响力会妨碍他们为婴儿提供文化一致性环境的努力。然而,当父母的成功开始渐渐危害到他们控制孩子目标和行为的权利主张时,时机就逐渐成熟了。从特别的角度来看,假设高贵者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不会产生破坏父母持续进行的对孩子攻击性控制方面的教育的影响。高贵者也不会证明一种不可靠的引导;他会对经验不足问题比较敏感,并且在孩子自己形成善的概念的背景下,帮助孩子作出慎重选择。将进行的对话如下:
父母:女儿,我告诉你多少遍了,你不该玩你哥哥的卡车。你应该玩布娃娃。
女儿:可为什么我不能玩卡车呢?
父母:我说得够多了!不许再说这些卡车之类的事儿了,这是我说的!
女儿:(哭泣)。
父母:这太可笑了。上楼回你自己的房间,一直待到你更懂事点再出来。(孩子遵从。门铃响了,高贵者来了。)
父母:你来做什么?
高贵者:我来和你女儿谈谈。
父母: 你想告诉她什么呢?
高贵者: 我想说尽管你试图压制她,可她想玩卡车也许是对的。现在,我能继续吗?
父母: 除非我对此事无话可说!
高贵者:好吧。你要说什么为你禁止我见她的行为辩护呢?
父母: 首先,她是我的孩子,不是你的。所以,滚出这儿!
高贵者: 你错了。与椅子不是“你的”无主物的一部分相同,她也不是“你的”孩子。相反,她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公民。
父母: 你怎能如此肯定?
高贵者:当我在按门铃的时候,她不是在质疑你的权威的合法性吗?
父母: 是的。但她必须遵守特别限制。
高贵者: 我没否认这个,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公民,你的女儿有权享受与她的对话和行为发育一致的最低限制性环境。这个标准的公平适用使你无权拒绝我接近她。(说明这个主张为与父母的控制与引导的剩余权力相一致。)
父母: 假设出于这场讨论的目的,我接受你的理由。接下来该如何?
高贵者:那你就得给我提供一个符合自由主义进程的、将我隔绝在外的理由。比如,你不能断言你的女儿对我的对话毫无兴趣。
父母: 相反,你的言论只会鼓励她对卡车之类的兴趣。
高贵者: 可那有什么错呢?
父母: 女孩子玩卡车就是件不好的事。
高贵者:我恐怕你得做的比那还好些。因为我认为对她来讲玩卡车是件好事。
指挥官:鉴于现在的意见冲突,我认为你们的主张都不能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中权力拥有者的合法理由。
父母:好吧,我们看起来陷入了僵局。虽然我还是不得不提供一个将你与我女儿隔离开的中立性理由,可你也该提供一个自己应对她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中立性理由。在你与她交谈之前,你必须回答我的合法性问题:你凭什么有权利寻求那种权力。
高贵者:问得好,可我有答案。我觉得每个公民都拥有一种原始权利,自己决定哪种交流在他看来是金玉之言。毕竟,每个公民都与其他人一样好。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中立性会作出解释,否则就能得出结论:没有第三方拥有审查每个公民都身处其中的符号交流顺畅的权利。
指挥官:这个意见没有违背中立性的地方。对于当前的辩论,还有什么要说的?
高贵者:除非父母提供一个审查我与女孩沟通的中立性理由,要不我就拥有与女孩交谈的权利。如果女孩与我都认为把时间花在交谈上是件互惠互利的好事,那我们就有权在一起交谈。
指挥官:好的,高贵者,我认为你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对话义务。如果父母无法提供一个中立性理由,证明他对女儿的道德准则和认识进行垄断是合法的,那你就会获得你寻求的权力。
父母:也许我最好要重新考虑下之前为讨论之目的而做出的让步。也许我能使我的同胞们相信,高贵者的干扰会破坏我们培养女儿自控能力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而且与此同时,考虑到女儿的经验不足,我对高贵者能否是个可信赖的向导持怀疑态度。
指挥官:此类经验主义论据通常都是受欢迎的;但是,理所当然地,高贵者也必须得到同等机会展开叙述自己对相关因素的看法。
这个对话本身蕴含的意义已超出引起对话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冲突。对话将成为下一章的基础,而我们在下一章将从更普遍的角度探讨憎恨自由主义审查的所有表现形式。不过目前,关键问题是对话对所有园艺学教育理论的批评。父母不得把孩子的反抗视为一种破坏他们私人花园美感的杂草;他们必须逐渐承认其他人为孩子提供文化资源的权利,这些文化资源可能将为孩子脱离父母规范、形成自己的特性打造一个开端。事实上,我们的上一个脚本也只适用于中等教育的最早期,此时女儿遇到父母显示权威所能做的只有哭泣。逐渐与外面的世界发生接触,会为她提供在对话扮演更主动角色的文化能力,她会坚持自己有权利与高贵者或任何在澄清她逐渐演进的自我概念方面有用的人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会代表自己说得更多,可能开始要求从父母和高贵者那里取得独立,一直到那一天她认为自己已获得对攻击性的足够掌控力,拥有对大千世界的丰富经验,能提出权利主张确定并使他人相信自己的善的概念,就像自由主义国家的所有其他公民一样。
然而,在强调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人际关系紧张和对话的核心时,我不想夸大自由主义对父母权威的敌意。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由主义教育不是想要劝服孩子,让他相信父母的价值理念是腐朽不堪的,所以让他最好转换至某些描述未来理想人类行为的官方意识形态。它的目标不是个人转变,而是为孩子提供将来在自我界定时有用的资源。尽管高贵者来访了,但女儿可能会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归根到底父母还是对的,并且逐渐认识到玩卡车对一个逐渐长大的女孩来说确实是不合适的。这种孩子教育的自由不是由她自己决定的后果来衡量的;唯一的衡量指标只能是她获得文化资源的程度,那些文化资源提供了在她看来对弄清早先的反抗有帮助的方法。在遇到选择性文化解释的可能性时,女儿接受了父母的模式,那这就是教育交换的最合法的结局了。可以肯定,自由主义指挥官必须承认父母与高贵者的价值理念应同样有权受到尊重。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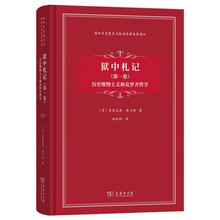








——约翰·罗尔斯
★在我们假想的旅程结束时,我们得以看见一个既坚持个体权利,又信守民主决策的世界;一个利用政府权力打击剥削根源,同时又对官僚专制的危险保持清醒认识的世界;简而言之,我们对中立性对话的信守使我们走向熟悉的政体形式——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
——布鲁斯·阿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