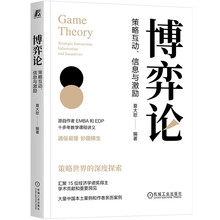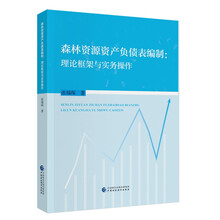《老子经济学》:
这一章揭示了科学原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它认为,“道”本身无法用语言加以表述,只能反复体悟,因为任何对“道”的表述都存在缺陷。这里所说的“道”,可认为是现实世界中各种事物及其运行的规律。
对于“经济学”(Economics)而言,面临同样的问题:各种经济学理论只是对真理的一定程度逼近,均存在缺陷,可能被推翻。道理很简单,现实即是“道”之本身,经济学原理(或理论)则是用来“名”现实(“道”)的名相,“无”是现实,“有”是理论,我们可以用理论分析现实,但理论不等于现实,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均与现实存在差异,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成立,离开了约束条件,理论很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时常探究“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变化,不要执著于理论。
下面举例说明。对于某种植物,我们给其赋予一个名称为“芭蕉”,并做出如下解释:“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宽大,叶和茎的纤维可编绳索。果实也叫芭蕉,跟香蕉相似,可以吃”,并且将这一段话作为通用定义收入《新华字典》。那么,当人们进行交流的时候,只需使用“芭蕉”这一词语,交流的各方就明白所讨论的是什么植物。但是,如果没有创造出“芭蕉”这一通用词语,人们谈论“芭蕉”的时候,需要花费很大气力来描述“芭蕉”的特点,即便是重复前述定义,也让我们觉得很累赘。
由此不难明白:当我们邂逅一位陌生人,首先会根据他的一些外显特征贴上“标签”,比如,他是博士,很有学问;他是四川人,能吃辣;他是上海人,为人小气。推而广之,学历、职称以及一些自然特征(衣着、肤色、年龄、性别、生长环境等)都被当作“标签”,用以判断某个人的性格、能力以及其他特征。尽管孔子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即“标签”不一定准确),但我们还是习惯于给他人贴“标签”,因为“以貌取人”是节省成本的做法。现实生活中,警察习惯于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外来人口、失业者、低文化程度者以及刑满释放者,无非是试图以较低的成本破案。事实证明,这种思路是可取的。由于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罪犯不会将“犯罪”两个字写在自己的脑门上,每个人看起来都是“良民”,那么,只能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犯罪嫌疑人。但是,如果警察调查每个人,则时间、金钱等成本非常巨大,难以承受。警察利用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标签”,可以直接排除绝大多数犯罪概率很小的人,将目标锁定犯罪概率较大的一小部分人,从而以较少的成本破案。
当然,人类所创造的词语、所提出的各种理论,是对事物的称谓和描述,在大大简化交流成本的同时,也显现诸多缺陷。称谓只是事物的符号,而不是事物本身。当称谓被创制出来之后,人们总是倾向于按照称谓的常规意义或者想当然的意思去理解具体事物,具体事物的独特个性因此很容易被淹没在称谓的常规意义之中。就说芭蕉树吧,它与香蕉树的外观非常相似,我这个北方人就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所以,人们需要表达的思想越是精微或需要描述的事物越是复杂,对语言f或称谓、理论等)的缺陷越有感触,以至于很多人倡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既然我们所创造的语言文字、各个学科所提出的理论,只是尽可能地接近“真理”,我们不应该盲从任何理论,要不断地结合实践去筛选理论,并创造出更好用的理论。即使日常看到的乌鸦全部是黑色的,我们如何敢于断言“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即使知道过去每天太阳都从东方升起,我们又如何能够肯定明天太阳还会从东方升起? 上述道理很浅显,但是很多学者在运用理论的时候往往忽视假设条件,把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加以运用。这种失误,不仅做投资分析报告和经济研究报告的人容易犯,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也难以避免。著名的“李嘉图恶习”就是一个典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把李嘉图的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