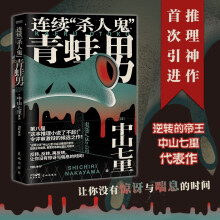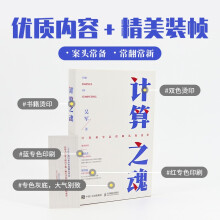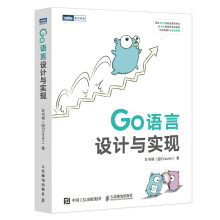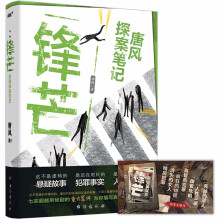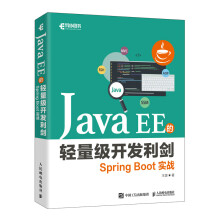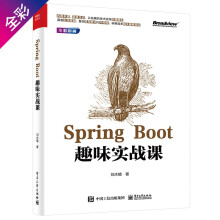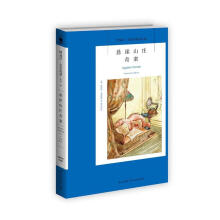在这一前提下,由日名制进而考察商代王位的继承法,最受瞩目的现象便是历世商王不论是父子相继还是兄弟相及的,也不论是“内子”还是“外子”,都毫无例外地使用日名,所有商王无一例外。照我们的意见,十干日名是王室内婚群的标志,亦即商代诸王内婚诸妻及其诸子所组成的群体的标志,是表明这一群体成员姓族身份的符号系统。由此便可得出一个最为根本的结论,即商代王位的傅承在常规状况下是严格控制在内婚范围之内的,祇有内婚诸子纔能继承王位。也就是说,凡王位继承者必须是前王的“子姓”配偶所生,通常异姓配偶之子不预。其中凡兄弟相继为王者,诸人亦必是上代王的内婚诸子,虽不同母而皆同父。对于这一点,如果允许反过来说的话,那么我们以为日名制便是王位在内婚群中传承的铁证,也是王位继承法植根于传统社会风俗的最为根源性的特征。这里权且分言之,列为商代王位继承法的第二个特点。
在“子姓”部族内部通婚的特定范围之内,王位传承还根本谈不上会涉及嫡庶问题,因为内婚诸母和诸子都不分嫡庶,诸子在原则上都有继承王位的权力。卜辞所见的妣名绝大多数都不与下代王名相应,这点又可与王位在内婚群中传承互为反证。征诸其实,在当时特殊的贵族家庭结构中,内婚诸母与诸子之间本无亲生观念(这点当然主要须从制度上看而不能仅从心理上说),故亦无所谓嫡子继承制,笼统地说商代已通行嫡长子继承制则尤其不合于历史实际。前述嫡庶制问题虽然还需要进一步论证,而现时的材料还祇能说明,商人的嫡庶之分尚远未达到制度化的程度。如果由卜辞“多介”引出嫡庶之分的机制,那也只能说在内婚群与外婚群之间已自然产生出嫡庶的萌芽,而还完全不是人为的规定,当然更不可能像后世那样,规定某子为“嫡”,其余同父同母或同父异母兄弟都是“庶”。而与王位继承法的第一特点相联系,内婚诸子的继位原则上也是限定在直系家庭之内的,不能扩大到同世内婚兄弟所建立的旁系家庭。在商代王位的传承系统上,凡兄弟相及者,事实上存在着复传兄之子与直传弟之子的两种情况。按直系传承的原则,在后世的观念上,本应以复传兄之子为正;而直传弟之子者,或因特殊的情势造成,或者在商人的观念上,同属内婚群的弟之子继位也不违反直系传承的原则。这后一种情况,还不能与后世所称的大权旁落相比附,因为内婚制的根本机制不过在于保证权力和财产由直系传承,兄弟之子都是近亲直系。而且即使称之为大权旁落,也是正常现象,后世姓族皇朝仍时有发生,但皇统一般不会因此而中断。
考虑到历世商王的大部分出于甲、乙、丁三宗,对于母系姓族传统在继承法上的影响就是不可忽视的。商王族既是“宗”、“族”交叉的群体,那么母系宗法就不可能不对王位继承发生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时很可能还相当重。只是对此未可仅着眼于商代女性的地位和权力,恐怕更应注重当时宗族分布和习惯法的力量。“子姓”内部的宗际通婚,本质上还是族际通婚,而宗群的分布可能并不均衡,某些强势支族尤以甲、乙、丁三宗的成员为多。这样,母系宗法的影响就通过父系族群的势力显现出来,王室势力是靠一些强势支族的支持维系的。十干日名本身不是这些强势支族的名号,而这些强势支族可能各自包含某些不同母系的宗派成员较多,并且在其聚居地可能还各立有从母系转向父系的时代继承下来的母系宗庙。如此,久而久之,俗间或亦以其母系宗庙的日名称其族。这也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遗迹,以致后人误认为十干日名即是划分父系群体的称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