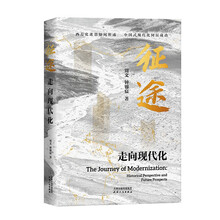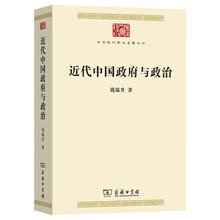第一章 迫于无奈的选择与国族观念的萌发
——晚清王朝国家时期的国族构建(1840—1911)
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开启,是晚清社会面对西方民族国家强势介入做出的痛苦而又无奈的抉择。原有的“天朝上国”心态和 “天下体系”在一次次的失败和屈辱下,逐渐松动、蜕变,直至坍塌。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晚清政府、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都做出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回应。而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对中西差距的认识也更为深刻,构建民族国家,形成强有力的国族,成为中国摆脱落后,重新跻身世界舞台的最后选择。然而面对国族这一崭新的民族形式,人们对其名称符号、评判标准和构建方式都有着较大的争论。但在纷争的过程中,人们对国族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并且诞生了国族名称—中华民族。同时,晚清政府也做出了自身限度内的努力,但最终没能实现英国“光荣革命”式的华丽转身,黯然离场。作为国族构建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的国族构建思想和措施,对于后来的国族构建与发展影响深远。
……
第二节 王朝限度内的国族意识萌动
王朝国家以一种天下观念想象着世界,但却忽视了外部世界自我想象的方式早已发生了转变。近代资本主义在国族基础上建构的民族国家体系已在西欧基本确立,并进行着急剧的对外扩张。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却以闭关锁国的方式维持着帝国表面上的辉煌。最终,大清王朝对世界的回避并没有换来世界对他的遗忘,西方国家用枪炮叩开了大清国门,将其从天朝迷梦中惊醒。而大清帝国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也开始被迫应对,在这一进程中,近代中国的国族意识也开始在传统的限度内萌动。
一、王朝向民族国家体系的妥协
天下观念是王朝国家构建自身与外部关系的基本态度,但对于国族构建而言,这种观念却是需要首先击碎或清除的。王朝国家的内部构成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具有想象为无限的可能。因此,对于王朝国家而言,对等、有限并且稳定的“他者”是不存在的,通过接受儒家文明都可以转变成自我的存在。而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是以相互间确认对方的主权和领土界限为前提的。“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 拥有主权是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一个没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民族国家。”[1]因此,从本质上讲,民族国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总是有限的。而这也决定了,作为民族国家内部人群共同体的国族也是有限的。如同安德森所言,“民族(nation)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使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2]“世界史并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4]而这一过程却始终在一种拒斥与无奈中进行着。
应该说,伴随着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扩大,天下观念就开始屡受冲击,但辉煌文明的惯性使统治者不能也不愿实现自我观念的更新,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进行着理论的勉强修补。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佛教的世界图像曾一度影响了中国中心的天下观念。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中国中心的观念,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四夷仍然处于中国文明的周边。[5]明朝开始,伴随欧洲殖民者和传教士的来华,开始带入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地理知识。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这些书籍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相信其他文明的存在,但仍坚持中国的世界中心位置。理学家李光地认为,“中国不可言地之中,……可言得地之中气,所以形骸端正,文物盛被”。[6]《皇朝文献通考》中的“四裔考”认为,“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国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清王朝虽然认识到了存在其他文明,但把这种文明也看做是“夷”,希望用华夷之辨思想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明末清初,先进的科技知识和军事技术也已经传入中国,并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但对于清朝的统治者,不但执着文化上的优越性,也不甘心科技层面的落后,所以炮制出了“西学中源”,与之抗衡。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本质上为了追逐贸易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殖民者在初期刻意迎合了中国的自负心态,“清初与荷兰、葡萄牙的直接交往,是严格按照传统朝贡礼仪进行的,清廷将西方国家视作朝贡国,加以怀柔,并用贸易作为羁糜的手段。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力求得到清政府给予贸易方便和特权,因此不惜为清廷效力,或讨好清廷,自认为属国”。[8]
但对于已经确立起民族国家体制的西方列强而言,“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国家实力得到迅速而显著地增强。随后,这些国家便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争先恐后地对外进行殖民扩张。”[9]这种非常态的对外交往方式始终是西方国家无法忍受的,伴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他们终于动用了最后的政治手段—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0]而这场决斗正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晚清王朝不得不在被迫与自觉中重新审视自身与外部的关系问题,其结果就是由天下观念向国家体系的收缩,这为国族的构建奠定了有限度的外围想象空间。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交往是在华夷之辨的逻辑中展开的,例如将英国称为“英夷”,视英国的使臣为“贡使”,并强迫其遵行贡使的礼节。而当清王朝认为英国使臣“贡表失词”,“抗若敌体”时,竟昭示英王,“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据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11]而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中,“英夷”已改称“大英国”,并且规定,两国官员来往“必当平行照会”。而《中英天津条约》更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内外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12] “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13]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中英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意味着与其他签约国之间的交往享有同样原则。1861年,清王朝设立专门机构处理西方国家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出资翻译《万国公法》,开始接受国际公法并以此来分析中外关系。同时,在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中,边疆地区是首先遭到冲击的区域,据学者统计,近代列强共侵占了我国340万平方公里土地,[14]并不断挑动边疆的少数民族同胞,妄图分离中国。“这使中国人在逐步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同时,也从反面强化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观念。”[15]而面对边疆危机,清政府也更加明晰了边疆地区的主权意识,对其加强管理,对比清朝初年,这也是国家观念增长的重要表现。
总之,承认国际交往上的国家平等,重视边疆领土的主权意义,逼迫清王朝具有了一定的民族国家观念。这是国族构建重要的初始动力,同时也为中国近代的国族构建确立了一个强势的他者。国族作为有限的共同体,是要通过他者来实现自我的确认,同时,他者的强势存在,又会成为国族凝聚的重要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转移内部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如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他者”的形象逐渐由夷转变成洋,而且也开始采用“华人”、“中国”、“华民”等词汇作为自称,显然包括当时清朝范围内所有民族同胞。
[1] 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3]《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 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4]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5] 邹小站:《华夷天下的崩溃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变迁》,《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6]《理气》,《榕村语录》,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1页。
[7]《皇朝文献通考》卷293,第1页。
[8]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00年版,第420页。
[9] 周平:《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6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11]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0页。
[12]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第102页。
[1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第96页。
[14] 马大正:《清代边疆史研究当议》,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5] 周平:《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6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