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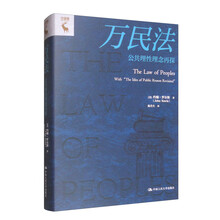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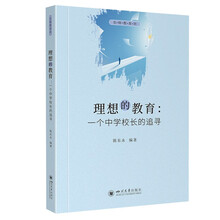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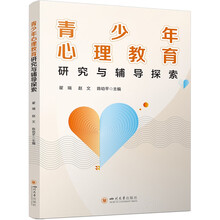
第一章 人权:不完备的思想
1.1 启蒙运动的人权计划
“人权”这个术语的使用开始于18世纪末(例如,在法国1789年颁布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中),但只是在20世纪中期才广为流行。在18世纪末,人们谈论的是“自然权利”而不是“人权”。这两个术语来自同一个连续的传统,具有大致相同的外延,尽管内涵不同。一般认为“自然权利”来自“自然法”。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要说“人权”原本来自于什么则更为困难。
自然法学说在古希腊和罗马都各有根源,不过,对它的最有影响的表述是由托马斯•阿奎那提出来的。上帝已把各种天赋的自然倾向置于一切事物中,不过,只是在人那里,他才植入一个理性倾向—把引导行为的各种准则产生出来的倾向,比如说如下准则:要维护自己的存在;要繁衍我们的种类;要寻求对上帝的知识并崇拜上帝;要和平地生活在社会中,等等。这些准则和其他准则构成了自然法,而自然法则充当自然权利的标准。然而,阿奎那在这里提到的“权利”根本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后者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一项资格。相反,阿奎那所提到的“权利”是一个事态的一种性质,即这个事态是正当的、公正的或公平的。对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阿奎那有很多论述,但他是否持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权利概念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权利”这个术语,尽管在中世纪晚期就开始出现了,但直到17世纪和18世纪才得到广泛应用。让我回顾一下从阿奎那到启蒙运动的一些发展阶段。把人类引向善的一个主要的自然倾向显然就是合理性,它引发了“遵循实践合理性”这一准则。这个准则大体上缺乏道德内容,更像是获得道德内容的一项指令——实际上,这项指令无所不包,以至于有取代所有其他准则的危险。如果人类理性已足以把自然法鉴定出来,那么在自然法中还需要上帝来做什么呢?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托马斯主义传统在17世纪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对此给出了一个回答。虽然人类理性让人类具有了某种相对于上帝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有限度的。人类确实可以不依赖于上帝来理解自然法的内容,不过,他们所理解到的东西只是因为上帝的意志才有了律法(一种具有力量的命令)的地位。
新教徒雨果•格劳秀斯采取了进一步的举动,他论证说,甚至无需诉诸上帝,就可以说明自然法如何向我们施加了义务。于是,格劳秀斯就获得了作为自然法的现代世俗理论的奠基者的名声。他写道:“我们一直在说的东西[即:存在着自然法,自然法向我们施加了义务]将有某种程度的有效性,即使我们竟然承认了只有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承认的东西—上帝并不存在,或者人类事务与上帝无关。”格劳秀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绝没有让自己做出这种“邪恶的承认”。不过,在他看来,不管我们在宗教问题上持有什么信仰,通过那种对我们所有人都开放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把自然法确立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理性本质来行动,必须做各种有助于维护社会的事情,而社会尽管与理性相一致,却是由像我们这样在动机上不相一致的成员构成的—一方面,我们天性渴望社会,另一方面,自我利益又是我们本性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要素,因此就会危害社会。
就像格劳秀斯一样,塞缪尔•普芬多夫认为,尽管上帝的启示可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自然法,但“甚至在不借助于启示的情况下,自然法仍然可以由理性能力来加以研究并确定性地得到证明”。在他看来,有一个问题特别需要经验研究,那就是:既然人类是一种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l sociability)的生物,那么,为了把一个合理的稳定的社会从那种生物中产生出来,需要哪些准则?
经过这些阶段我们就到达了启蒙运动时期。按照我的理解,启蒙运动开始于17世纪最后十五年左右,到18世纪结束。在《政府论》中,约翰•洛克仍然在其论证中赋予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以中心地位,并且也认为自然权利来自自然法。然而,洛克几乎没有去关注自然权利是如何从自然法中引申出来的;他把自然法的语言当作一种恰当地确立起来、相对不成问题的说话方式来使用。在他看来,理性本身就能把根本的道德原则确立起来—实际上,能够确定地把它们确立起来。对于洛克来说,这种推理的核心,就像他之前的普芬多夫所说的那样,是要对一些律法进行经验研究,而为了能够把有着非社会的社会性的个体转变为一个恰当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成员,就需要这些律法。在这个推理过程中,我们无需诉诸任何关于人类生活的目的的观点——实际上无法成功地诉诸这样的观点;洛克认为,就人类生活的目的而论,理性的人们会有分歧;因此,尽管一个关于最高善(summum bonum)的信念在古典思想和中世纪思想中都处于核心地位,不过,在这里,人们对它的关注至多也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它不能赢得普遍同意,因此就不能有效地引导在思想观念上具有本质差别的社会成员。洛克确实不时提到上帝,但那是自然神论者的上帝:上帝就是宇宙的设计者,让这台巨大的机器开始运转,然后就退出场景—不再干预,不再发布启示。在《政府论》中,洛克主要关心的是对统治者的武断行为进行道德约束。于是,毫不奇怪的是,他所关注的自然权利涉及在没有正当的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是君主恣意统治人民的三种最常见的方式。
……
詹姆斯·格里芬谦虚地视自己的著作为抛砖引玉,希望学界能更多地对人权的现代阐释进行理论批评,但本书的意义远不止如此。本书在学术上非常严谨,在智识上富有挑战性,且论述非常清晰。正是这样的书令哲学影响我们的世界。
——阿兰·贾德,《观察家》
詹姆斯·格里芬的新书是对人权哲学的重要贡献。他在书中为自己构思精妙的人权论述做出了辩护,使得本书成为了人权领域专家的必读之物。
——威廉·J. 塔尔博特,《圣母大学哲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