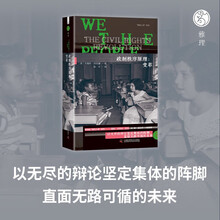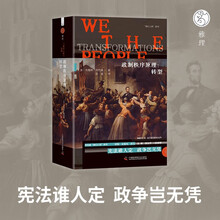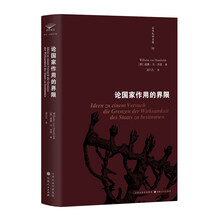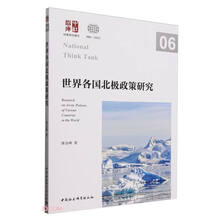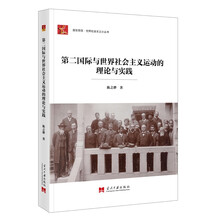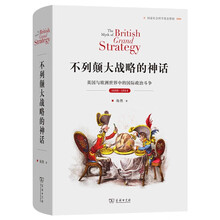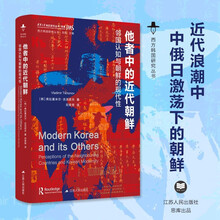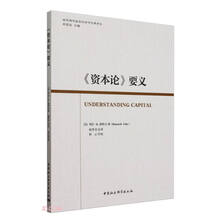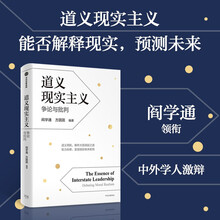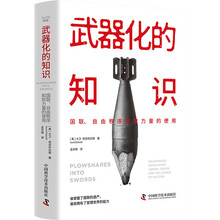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美国因素”在中国周边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因素。“美国因素”对崛起的中国而言究竟是负面居多, 还是正面居多?抑或正负两面皆有?在现阶段,中国究竟如何客观评估和有效利用“美国因素”?这是今天和未来中国已经绕不开的一个课题,而这一课题在2010 年之前似乎并没有那么紧迫。
曾记得,2003 年之前的几年里,时任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刻意操弄“台独”思潮和行动,将两岸关系推向几乎万劫不复的边缘。2003 年,时任中国总理访问华盛顿,与美国达成联手制约陈水扁“台独”的共识。此后,台海局势开始逆转,陈水扁的“台独”倾向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直到2008 年马英九上任。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当时华盛顿与北京的联手,陈水扁的“台独”嚣张不可能被抑制。从这个意义上,你能说在两岸关系上,“美国因素”是负面的吗?
也曾记得,2012 年12 月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面对中国崛起的态势,凭借日本国内日趋保守的政治基础,采取对华日益强硬的立场,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没有争议”立场,丝毫不做妥协;第二,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中韩和周边邻国的情感底线;第三,以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
在这一背景下,不但中日领导人峰会全面停止,而且就在日韩这两个同盟国之间,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一些国际场合,就连把眼皮抬起瞧一眼安倍都懒得,更遑论与安倍握手言和了。但2014 年下半年,安倍忽然一反常态,公开站到电视镜头前声明,他在历史问题上将继续坚持之前历届日本内阁的立场。再往前查一下记录,原来美国私下向安倍施加了压力。这从本书第四章透露的美日智囊电视激辩中,包括美国智囊对安倍连任后的期望表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你能说在中日关系上,“美国因素”纯粹是负面的吗?
当然,无论是两岸问题还是钓鱼岛问题,其根源都可追溯到“美国因素”。或者说,这些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也主要是由于“美国因素”使然。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有其在亚太地区自身的战略利益。从这些利益出发,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维持一种适度的“不平衡”。在两岸问题上,无论是20 世纪50 年代将台湾视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还是后来希望通过支持民进党长久维持两岸的分治、分裂状况,均无不出于这一战略目的。在中日关系和南海问题上,美国的战略利益也大抵如此。
但这不等于说,两岸的纷争或中日矛盾、南海冲突达到擦枪走火的边缘,美国将依然维持其原有的战略底线和立场。原因很简单,若地区冲突突破美国能容忍或承受的范围,势必将冲击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因素”中调唆的一面会变成稳定局面的一面。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03—2008 年间,华盛顿愿意与北京联手制约陈水扁的“台独”,以及美国何以对安倍的修正历史问题的举措感到如此不满。这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2014 年当中国的981钻井平台深入南海时,尤其是当越南与中国有可能在南海擦枪走火时,
美国一再运用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
在施加压力,维持亚太地区适度平衡的问题上,应该说,美国没有特别的针对国家。对直来直去的美国人来说,其指针只有一个:谁打破平衡,就对谁施压。
但在风和日丽之时,美国的战略则有其明显的侧重点,那就是哪个国家是美国在该地区乃至全球的潜在对手,那就使用各种手段对其形成钳制。在今天,这个国家无疑就是迅速崛起的中国。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2009 年全面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和安全局势趋于全面紧张。
因此,对一般的中国公众来说,一个人性的感受就是,美国既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又在策略上与中国为敌。这一感受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其不完全的另一面。从上面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出“美国因素”的两面性,即既有调唆局势的不稳定一面,同时又有维持稳定的另一面。
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看透“美国因素”的两面性,将“美国因素”维持稳定的一面利用到极致。
仍以2003—2008 年间的两岸关系为例,陈水扁的追求“台独”引起北京强烈反弹,继而引发北京对台军事斗争的实质性准备。正是这种实质性的准备,让美国看到北京的底线,也看到突破这一底线可能导致的后果。北京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底线,是将“美国因素”的稳定一面发展到极致的关键因素。
以此来看未来的地区安全格局,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中国国家实力的外延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及南海一些国家均有疑虑、恐惧乃至敌意产生。对中国来说,不走出去显然不行,但走得太快也不行。面对日本和南海一些国家的疑虑和敌意,中国必须有适度的冲撞,方能逐渐改变由原有强国确定的“现状”。但这种冲撞却又必须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进退有据,宽紧适度。没有适度的冲撞,“现状”永远不可能被打破。但冲撞过度,则可能导致所有对手的联手反弹。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适度冲撞的战略作用发挥到极致,同时又正好在美国的可控和可容忍范围之内?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地区对手挑衅,中国如何反弹?第二,中国如何主动出击?
前文阐述的陈水扁和安倍当年的挑衅,均属于对手挑衅,中国被迫反击。试想,若中国不将反击幅度拉到最大,美国怎么可能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类似981 钻井平台的风波,则是中国主动出击,但遭到周边国家的反弹和美国的“阻击”。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崛起对世界“现状”的改变是渐进的,必然伴随着对手的“阻击”和中国的主动出击。无论是对“阻击”的反弹,抑或是主动出击后遭遇的“阻击”,其面临的问题都是究竟是“进一步,退两步”?还是“进两步,退一步”?将冲突和紧张的力度拉到极致,然后做出适度的妥协,究竟能达到这两种境界里的哪一种?
这是一个需要中国、美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探索的问题,也是各方在冲突中妥协,在妥协中共同建构“新常态”的过程,更是各方人们的心态逐渐成熟的过程。
若干年后再回头看,人们对今天发生的一切冲突就会有一种相对释然的感觉。
但2015—2017 年,却将依然是中美双方互相测试战略心理底线,并在行为上充满冲突风险的几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