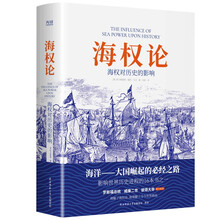《中山大学政治学丛书·政治哲学:问题与争论》:
二、政治义务及其相近概念一般来说,如果统治者或政府具有统治的权利,那就意味着公民有服从的义务。这种服从国家及其法律的义务,就是政治哲学中所说的政治义务。由此看来,政治义务主要与政治权威中的“权利”这一要素相关。很明显,如此理解的政治义务不同于法律义务,后者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所需要履行的义务。而政治义务的问题则在于,我们是否应当服从这样的法律本身。这个问题显然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可能对法律本身,尤其是对法律背后的立法者资格提出道德判断或道德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义务(如果我们确实负有政治义务的话)显然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
如果公民确实负有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义务,那么即使国家的法律、政府的命令不符合公民自己的利益,甚至不符合公民自己对正义的判断,他都应当服从。道德难免与自我利益相冲突,而且此时我们应当克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奉行道德的要求,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或者不如说,这就是道德生活的本来含义。但是,(至少是某些情况下)当我们的正义信念(包括我们经过理性反思仍然坚信不移的信念,甚至是道德上确实正确的信念)对我们提出相反的要求时,说我们仍然应当服从与之不一致的法律,这该如何理解呢?这岂不是要求我们违背道德吗?这个问题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有关。每个人的正义观或道德信念可能存在冲突,因此政治上我们常常需要有一种作出集体决定的程序,如果这种程序本身是正当的,而且也是我们所接受的,那么,按照这种程序作出的决定即使与我们深刻持有的信念相冲突,我们也许就仍然有义务去服从。宪政民主制度之下的多数决定原则其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人发现自己在道德上有义务服从不正义的法律,这在宪政民主条件下是一种常见的情形。每当属于少数派的人在一项法案上出于正义的考虑而反对多数派时,情况就是这样。”少数派或少数派的代表可能从这样的法案中受益,但他们仍然可能基于正义的考虑而反对这项法案。但只要这项法案的通过没有违背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和立法程序,少数派就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服从这部获得通过的法案。
还有一种对政治义务的更宽泛的理解,即认为除了遵守法律而外,政治义务还包括以其他方式支持国家的政治机构的责任,例如在国家防卫中尽一份责任,等等。但在政治哲学中,前一种狭义的政治义务概念才是理论关注的中心所在,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政治生活而言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政治哲学要为政治义务提供一种一般性的解释,它就应当证明一国之中的每一个国民都应当承担这样的义务。例如,如果我们只强调在国家中明显受益的部分国民负有这份义务,而利益受损的那部分国民没有这份义务的话,那么政治义务就完全转换成了一个利益算计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把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撕裂开来了。此外,政治义务既然是服从国家及其法律的义务,从理论上讲,义务的主体当然也就是特定国家的成员,而义务的对象就是这个特定的国家。不过,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政治义务的这种“特殊化”要求,为政治哲学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挑战。因为它意味着,如果我们仅仅立足于一个一般性的道德原则,例如一种明确的正义原则,就很难为这种特殊的义务提供最终的说明。换句话说,政治义务的特殊化特征“使任何想从诸如一般的功利或正义等这类更高层次的普通道德标准引出政治义务的企图变得困难了,因为通过服从自己国家的命令而使一般功利和正义毫无差别地获得最佳实现,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这种一般性的原则并不一定把我们的忠诚引向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可能引向满足这条原则的所有国家(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有多个国家都满足或接近于满足某种原则要求)。因此,一种有效的政治义务理论必须在强调其道德维度的同时,注意其特定的政治维度,即把个人与其所属国家之间的特殊政治关系这个维度考虑进来。
政治义务的概念还会引起另一个困惑,因为它只是一般性地强调服从国家及其法律,但我们凭经验就可以知道,有时候,一个国家的部分法律可能存在严重的道德缺陷,政治义务是否意味着我们对这样的法律也应当服从呢?上文对宪政民主国家少数派服从不正义的法律的义务所作的解释可以为此提供部分的答案。但这个回答似乎仍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服从的义务,就有可能迁就了一个国家内可能存在的严重不正义,从而有可能封闭了道德进步的空间。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宪政民主国家内,一旦批评某些不正义的法律的观点在社会中占了上风,人们便有机会废除或修正这些法律。不错,这一点常常被当作是宪政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优点。但有人难免会觉得,这仍然是让残酷的实践压倒了道德上的要求。这就涉及与政治义务间接相关的问题,即公民不服从,对此,本书将在第五章第四部分专门讨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