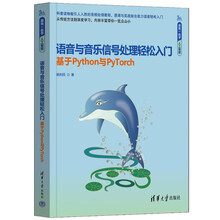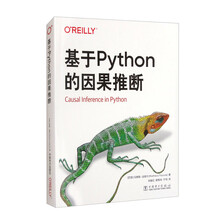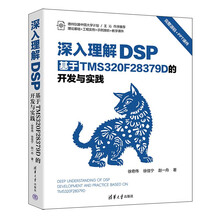我在向贵族说教,我指的是那个站在人类的宝塔尖上,而又深深了解下层人民的痛苦和需要的人。他很了解卡弗人①,他们按照一种特殊的韵律在布匹里织图案,这些图案只有在拆散布匹时才能看得到,他了解织毯子的波斯人,绣花带的斯洛伐克农妇,用玻璃珠和绸子编精彩东西的老太太。这位贵族随他们去,他知道,他们工作着的时间是他们的神圣时间。而革命者会来到他们身边向他们说:“这都是蠢事。”就像他会从路边的十字架上把那小老太婆扯下来,告诉她:“根本没有上帝。”贵族中的无神论者却相反,他在经过教堂的时候会举起他的帽子。
我的鞋子上布满了用扇贝和窟窿组成的装饰,鞋匠做了这些装饰但从来没有为它得到过报酬。我走去对鞋匠说:“你每双鞋要价30克朗宁。我要给你40。”我的话把这个鞋匠送上乐陶陶的云端,他将用手艺和材料报答我,远远超出我加的那些钱所该得到的。他很快活,快活很少进他的屋。有了一个人了解他,尊重他的工作,不怀疑他的诚实。他已经构思成了那双鞋,他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弄最好的皮子,他知道哪个手艺人能做这双鞋,这双鞋应该如何以最雅致的方式布满扇贝和窟窿。这时候我对他说:“但是有一个条件,这双鞋必须是素净的。”我的话又把他从乐陶陶的云端扔进灰心丧气的深渊,他可以少辛苦一点,但是我剥夺了他的乐趣。
我在向贵族说教,我容忍我身上的装饰,如果它们使我的伙伴高兴,他高兴我就高兴。我可以容忍卡弗人的、波斯人的、斯洛伐克农妇的和鞋匠的装饰,因为除了这些装饰之外他们再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生存的较高之点了。我们有取代装饰的艺术,在一天的烦恼和疲劳之后,我们去听贝多芬或者去看特里斯坦。①我的鞋匠不可能这么干,我不能剥夺他的乐趣,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能够给他乐趣。但是一个听了第九交响乐的人,坐下来设计糊墙纸的图案,那么,他不是一个算命的骗子就是一个堕落的人。别的艺术因为没有装饰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高度,贝多芬的交响乐绝不是穿着绫罗绸缎、带着花边走来走去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今天还穿着天鹅绒外套到处走的人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插科打诨的小丑或者一个油漆粉刷匠。我们已经成长得更雅致、更精妙了。狩猎的游牧人必须用颜色来区分他们自己;现代人用衣服当面具。他的个性已经如此强烈,以致已经不可能表现在穿戴上了。摆脱装饰的束缚是精神力量的标志,现代人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用古代的或异族的装饰,他把自己的创造性集中到别的事物上去。
……
展开